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王振国:守典籍之根 传岐黄薪火
2026-01-30
大众日报 28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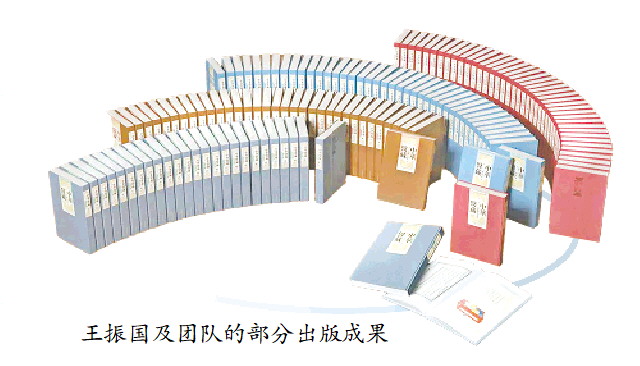 王振国及团队的部分出版成果
王振国及团队的部分出版成果
济南冬天的暖阳,穿过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校园,照进图书馆七层的文献展示区。书架上,一摞摞厚重的古籍校注本、学术专著整齐排列,《圣济总录校注》《齐鲁医派文库》等成果的扉页上,都印着一个熟悉的名字——王振国。
站在展柜前,他的指尖轻轻掠过书脊,仿佛在触碰一段段沉睡的历史。“这些典籍是中医的根,我们这代人,就是要守好这个根。”岐黄学者、山东中医药大学教授王振国说。
那些“竹子扎根”的岁月
1979年秋,16岁的王振国背着简单的行囊,走进山东中医学院的校门。彼时,高考恢复不久,校园里满是求知若渴的面庞。
在学校,讲授《中医各家学说》的张志远教授给了他极大震撼。“张老号称‘活词典’,上课不用讲稿,随便一个中医话题,他都能滔滔不绝讲上几个小时,引经据典,如数家珍。”王振国至今记得,张志远教授谈论历代医家学术思想时的神采。“那时才知道,中医不只是把脉开方,背后还有这么深厚的文献积淀和学术传承。”
王振国毕业时,报考了张志远的研究生。1984年,他跟着老师开始南北东西的调研之旅。“我们走了很多地方,拜访老中医,搜集民间医案,那段经历让我对中医学术流派有了直观认识。”
王振国说,老师常说历代医家的学术思想都藏在文献里,不读透典籍,就成不了好中医。这句话,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扎下了根。
毕业后,王振国留校工作。1987年,该校获批两个博士点,一年只招两个博士生。王振国抓住机会,报考了徐国仟教授中医医史文献的博士研究生。简而言之,这个专业一方面是研究中医学术史,另一方面是做中医古籍整理研究。
徐国仟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的弟子,也是山东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开拓者,不仅医术精湛,而且重视文献整理,著有《黄帝内经素问白话解》和《伤寒论讲义》。“徐老告诉我们,文献是中医的基础之基础,没有文献传承,中医理论和临床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王振国逐渐明确了方向。“张教授带我走进学术流派的大门,徐教授让我深耕文献研究的土壤。”博士毕业时,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从事中医医史文献研究,而彼时的他不曾想到,这条路会那么艰难坎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医医史文献研究的低谷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同仁涌向临床,毕竟“看病能挣钱,文献研究既冷门又清贫”,许多高校的相关机构也被撤销。
山东中医药学院的“薪火”虽然保留了下来,但学科课时少、没项目,只能艰难生存。整个研究所十几个人,每年会议费总共2000块钱,平均每人每年不到200块。“十年都轮不上一个人出去开次会”,回忆起那段艰难岁月,王振国苦笑着说。
没钱出去,就闷在图书馆里看书、写论文。那时没有电脑检索,所有资料要靠手工查阅,他每天泡在图书馆,一页一页地抄录、整理,写下大量读书笔记。王振国说:“就像竹子扎根,虽然表面看不到生长,但地下的根系一直在蔓延。”
有人劝他:“振国,你医术也不差,去干临床早成名医了,何必守着这个冷门学科。”王振国也曾犹疑,但每次翻起恩师们留下的手稿和著作,想到他们的嘱托,就又冷静了。“老一代开辟的基业不能在我们手里断了,得把这份传承扛起来。”
坐惯了“冷板凳”,他养成了沉心静气做学问的习惯。许多关于中医学说和文献整理的论文,就是在那段岁月里完成的。“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要是那时放弃,就没有后来的一切了。”他感慨道。
平地起高楼拿到“国字号”
转机悄然出现。“学院”升格为“大学”后,学校决定冲击国家重点学科,而中医医史文献成为“种子选手”。30多岁的王振国,意外被推到了学科带头人的位置。“我刚刚入门,学科是什么都还搞不明白,校长说‘你年轻,就你了,带头往前冲’,我只能硬着头皮上。”
当时评选国家重点学科,申报者一般要先拥有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重点学科资质,而王振国团队却“一穷二白”。很多人觉得他们是异想天开,根本不可能成功。时任校长王新陆却力排众议:“我们没有,但我们可以争取。”
为了备战申报,学校组建了一支由20多位教授组成的“智囊团”,对王振国进行全方位训练。“汇报时间只有10分钟,每句话都要精准到位,既要讲清优势,又要突出特色。”王振国每天都要进行模拟汇报,教授们从站姿、表情、语气到用词,逐一提出修改意见。“有时一句话改十几遍,每个手势都要反复练习,持续了一个月。那段时间压力特别大,但成长很快。”
答辩当天,王新陆亲自担任助手,为王振国翻幻灯片。“那时没有普及PPT,答辩用的是幻灯机和塑料胶片,需要手动更换。”王振国回忆,校长当助手,这在全国学科申报中绝无仅有。
前期的充分准备加上出奇制胜的汇报方式,让申报获得了成功。“平地起高楼,一下子拿下了国家重点学科,而且全国当时总共只有两个中医医史文献的国家重点学科。”王振国至今记得,答辩结束后,专家们评价:“没想到山东的中医医史文献研究做得这么扎实,有传承、有特色、有潜力。”
有了“国字号”牌子,团队获得了省里和学校的有力支持,在人才培养、科研立项等方面都有了重大突破。而这段经历,也让王振国深刻体会到:“有时候,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只要坚持下去,就可能创造奇迹。”
2006年,王振国跟着校领导去北京出差,一个偶然的“蹭会”经历,让中医学术流派这一小众研究领域成为全国热门话题。
当时会议主题是中医学术特色与优势如何发挥,校领导因临时有其他事务处理,便让王振国代为出席。“我抱着学习心态去的,没想到居然还要发言。”轮到王振国时,他结合自己近期的研究,大胆提出:“从历史经验看,中医学术流派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力量。现在中医院校统一的教学体系、教材和临床模式,淡化了中医的特色与优势。”
何谓中医学术流派?王振国解释说,中医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各地用药、发病特征不同,理论也有区别和创新。比如广东常用五指毛桃,山东则多用地黄、阿胶,南方针对湿热,北方针对寒症,这些都是学术流派的特色。”
这一观点得到了与会人员的认同。不久,全国第一个中医学术流派研究项目就落户在了山东中医药大学。王振国带领团队,用了近两年时间走遍全国,调研各地学术流派传承和文献支撑情况,打捞出一部鲜活的中医学术史,并提交了详细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
2009年,他提出的政策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2011年,中医学术流派传承纳入国家行业规划;2012年,国家投入1亿多元支持全国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从一个偶然的发言到推动全国性的工作,这是我没想到的。”王振国说,这也让他更加坚信,研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要服务于临床,服务于中医的发展。
与此同时,齐鲁大地自古名医辈出,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整理和总结。“全国终于开始重视流派研究,咱自己怎么能落后?”王振国说。
于是,他又开始牵头推动齐鲁医派研究。“我们组织团队,搜集整理历代齐鲁医家的著作、医案,调研民间传承情况,总结齐鲁医派的特点和优势。”2024年,《齐鲁医派文库》正式出版,这套包含十几种著作的大部头,成为齐鲁医派研究的标志性文献。
这些成果,十年磨一剑。王振国说:“做学术研究不能急功近利,尤其是中医流派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沉淀,才能真正把根挖深、把特色凸显出来。”
手抄《易筋经》引出大项目
2010年,中医古籍整理工作座谈会在福建召开,王振国又一次抓住了机遇,这次同样充满戏剧性。
会议期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系王振国,听说山东有本珍贵的《易筋经》古籍,想请他帮忙复印一份。可他跑到山东省图书馆一瞧,那本书属于文物级,不能复印,拍照只允许拍六页。
这难不倒王振国。他回去找出竖格稿纸,按照古籍原貌,用繁体字一笔一画抄录下来,装订好寄回北京。“手抄古籍是家常便饭,没啥麻烦的。”回忆起来,他淡淡一笑。
没想到,这份专业、靠谱和执行力,打动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巧,该局计划进行中医古籍整理,有4000万元专项经费。“后来,问起我整理一本古籍需要多少钱,我说10万块钱。于是,局里立项整理400种中医古籍,项目设立办公室,我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牵头项目实施。”王振国回忆。
这是天大的好消息,但他深知,工作难度超乎想象。“经过多年的冷落,很多人都改行了,全国懂中医古籍整理的人寥寥无几。”当被问及三年能否完成时,王振国直言,“三年肯定不行,五年也很困难,关键是缺人。”
于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决定,人才培训也由项目办公室负责。吃了“定心丸”,他牵头制订了详细计划:先在全国九个省选拔七个课题组,然后进行系统培训。“古籍整理有其行业门槛,尤其是中医古籍,涉及很多特殊术语和用药知识,不能按照文史类古籍的标准来。”
从2010年立项到2018年完成,这项“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国家公共卫生资金项目,整整用了八年时间。“我们学校自身承担了70种古籍的整理任务,同时还要组织全国330多种古籍整理负责人的培训,包括版本调研、书稿审定等工作。”王振国说,那几年,他几乎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既要抓自己团队的整理质量,又要协调全国的工作,经常开会到深夜,节假日也很少休息。”
中医古籍整理的难点,远超常人想象。首先是术语的变化,汉代的词汇发展到唐代,内涵可能就变了,比如“痧症”,清代之前指的是传染病,现在却成了刮痧的“痧”。其次是地域差异,南北用药不同,同一味药在不同地区名称可能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些中医词汇,其他领域不用,需要专门考证。比如“剉”字,在中医炮制中是切成小段的意思,属于专有名词,而文史类古籍整理者会统改成“锉”字,这在中医古籍中绝不能改,否则就改变了用药方式,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王振国联合众多专家和机构,制定了《中医古籍整理规范》。“过去古籍整理都是个人行为,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借鉴文史界的经验,结合中医特殊性,反复修改完善,形成了大家公认的规范,作为培训的基础教材。”
最让王振国难忘的是《圣济总录》的校注工作。这部由宋徽宗赵佶主持编撰的宋代三大方书之一,将近300万字,版本有几十种,整理难度极大。“我们从2003年开始整理,一直到2018年才完成,耗时15年。”这部书是宋代以前中医学术的大成之作,涉及很多疑难问题。团队经常开会争论,一个词、一个字地推敲,每天对着屏幕修改稿子,大家眼睛都熬红了。
2015年,第一批120种古籍整理完成;2018年,400种古籍全部完成。项目成果总计8000多万字,所涉及的古籍均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整理出版过的重要医书。这些努力,不仅抢救了一大批濒临失传的中医古籍,也为中医传承提供了文献支撑。
与此同时,项目还为全国培养了一批中医古籍整理的后备人才。“从2018年开始,我们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国性培训,邀请专家授课。”统计显示,这些年全国发表的相关论文,其作者很多接受过相关培训或项目支持。
通过这项工作,山东中医药大学在全国中医古籍整理领域的学术地位基本确立。“后来,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最系统的中医药古籍整理保护计划项目《中华医藏》学术办公室挂靠我校,由我们负责培训和学术把关,这是极大的认可。”王振国表示。
如今,该校中医医史文献团队里,不仅有中医人才,还有科学技术史人才。“这个学科本身是交叉学科,需要历史学、文献学等多学科支撑。”王振国说,年轻人才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让研究更有深度和广度。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的健康观念、养生观念、治疗经验都是通过文献不断积累传承下来的。世界上很多传统医学都已断层,唯有中医传承不断,这离不开文献的支撑。“文献学是为人作嫁衣的工作,我们整理的典籍,谁都可以用,这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工作。”王振国说。
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一本本典籍上,也洒在王振国的身上。他知道,中医医史文献研究的道路还很长,但只要有人坚守,只要薪火不息,这束光芒就会一直照亮未来。正如他常说的:“文献是根,文脉是魂,守住了根,留住了魂,中医才能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