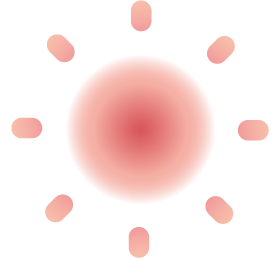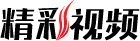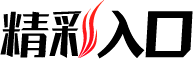云淡风轻(9)
2020-04-03 07:00:00 发布来源:湖南美术出版社
我一次一次来往的纵谷,火车窗外是多么奢侈的风景,银亮的新红,大概维持十天,金属光的银穗开始散成飞絮,白茫茫的,到处乱飘,在风里摇摆、摧折、翻滚、飘零、飞扬、散落—那是岛屿的芒花,很卑微,很轻贱,仿佛没有一点坚持,也绝不刚硬坚强,随着四野的风吹去天涯海角。它随处生根,在最不能生长的地方怒放怒生,没有一点犹疑,没有一点自怨自艾。据说农人烧田烧山都烧不尽菅芒,它仍然是每一个秋天岛屿最浩大壮丽的风景。
我读过比较专业的论文,最终还是想丢掉论述,跟随一名长年在古道上行走的旅人。在寒凉的季节,望着扑面而来的白花花的芒草,仿佛远远近近,都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美丽歌声。
是芦,是苇,是菅,是蒲,好像已经不重要了。在两岸蒹葭苍苍或蒹葭萋萋的河之中流,仿佛看见,仿佛看不见,可以溯洄,可以溯游,迂曲蜿蜒,原来思念牵挂是这么近,又那么远,咫尺竟真的可以是天涯。
“葭”是芦苇,也是乐器,让我想到初民的芦笛,他们学会了在中空的管上凿孔,手指按着孔,让肺腑的气流在管中流动,悠扬出不同音阶调性的旋律。
“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坻”“宛在水中沚”,歌唱的人其实没有太多话要说,所以反反复复,只是改动一个字,在水中、在水岸、在沙洲,到处都是蒹葭苍苍萋萋,摇舟的人重复唱了三次。好可惜,我们现在只能看到文字,听不到悠扬的声音了。
《诗经》是多么庄严的“经典”,但我宁可回到《蒹葭》只是歌声的时代,“诗”还没有被文人尊奉为“经”,“诗”甚至还不是文字,还是人民用声音口口相传的“歌”,还可以吟唱,可以咏叹,可以有爱恨,可以忧愁,也可以喜悦,是用芦笛吹奏,是在河岸芦苇丛中唱出的肺腑深处的声音。
《蒹葭》里重复三次“所谓伊人”,一个字都没有更动,“就是那个人”,就是那无论如何也放不下的日思夜想的“所谓伊人”吧。
没有“所谓伊人”,自然不会有歌声。
常常会念着念着“蒹葭苍苍”,想象两千多年前的歌声,像今天在卑南许多部落里还听得到的歌声,婉转嘹亮,有那么多的牵挂思念,一个秋天就让卑南溪两岸溯洄溯游开满了白苍苍的芒花。
《蒹葭》一定可以唱起来的。如果是邓丽君,会用多么甜美的嗓音轻柔地唱“宛在水中央”;如果是凤飞飞,会用怎样颤动的声腔唱出缠绵感伤的“溯洄从之”“溯游从之”;如果是江蕙,会把“蒹葭萋萋,白露未晞”两个闭口韵的“萋”与“晞”唱得多么荒凉忧苦。
想在岛屿各个角落听到更多好的歌声,听到更多可以流传久远的歌声。
歌声并不遥远,可以传唱的歌,可以感动广大人民的歌,一定不会只是口舌上的玩弄。动人的歌声,能够一代一代传承的歌声,必然是肺腑深处的震动,像阳光,像长风几万里,像滋润大地的雨露,传唱在广漠的原野上,传唱在蜿蜒的河流上,传唱在高山之巅,在大海之滨。数千年后会变成文字,会被尊奉为“经”,但是,我一直向往的只是那歌声,两千年前,或近在卑南部落,都只是美丽的歌声,并不遥远的歌声。(连载完。)
(蒋勋)
责任编辑: 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