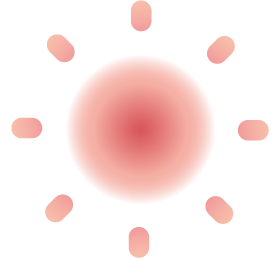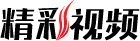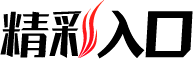齐鲁策论丨赵金旭:政府数字化转型,如何破解深层问题
大众日报记者 张浩 崔凯铭
2023-11-21 07:00:00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政府数字化转型再认识
□ 赵金旭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对整个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运作逻辑、价值观念等产生系统化冲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数字政府建设,并试图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府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政府的概念内涵
从各地的数字政府建设实践看,中国俨然成为一个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巨型实验场。爱山东、粤省心、渝快办、马上办、掌上办、指尖办、秒批秒办、一网通办、接诉即办等数字政府创新应用层出不穷、花样繁多,中国从一个数字政府建设的落后者、追赶者和模仿者,迅速跃升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引领者、创新者和驱动者。2022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数字政府建设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尤其是在线公共服务等指标名列全球第九。
数字政府是一个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而不断丰富、拓展和延伸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和数据库刚刚出现的时候,数字政府指的是“办公自动化”。随后的“三金工程”,以及“一站两网四库十二金”工程的建设,又使“电子政务”的概念深入人心。根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部门的定义:“电子政务是指政府或公共部门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向公众或企业提供信息或服务的过程”。这其实是站在工具论的视角上,按照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效率、效益、效能观念,对数字政府概念进行的理论建构。
而到了2010年前后,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移动政务”“社交政府”“指尖政府”“维基政府”“自助政府”“简洁政府”“平台政府”等概念纷纷又被提出。尤其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又使“敏捷政府”“智慧政府”“智能政府”“算法政府”等意涵融入数字政府的概念内核之中。
然而,现有对数字政府概念的理解依然是“碎片化”“微观化”“技术化”的,它并未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层面,对数字政府的理论意涵进行很好的阐释。笔者认为,我们要从政府数字化转型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对数字政府的概念进行更具“整体性”“宏观性”和“结构性”的理论建构。从这个角度来看,伴随政府数字化转型而来的,其实是国家与社会关系、政府与公众关系、党和群众关系的深度重塑或优化。
具体而言,政府数字化转型会通过“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权”两条路径,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众、党和群众之间,建构起新型的民情民意表达机制、社会风险感知机制、智能化决策辅助机制和精准化民意回应机制,从而建构起全新的基于大数据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结构。而这种社会治理结构是与农业社会的“单向控制”和工业社会的“分权制衡”迥然不同的,它是一种基于数字协商的全新的社会治理模式。
所谓“技术赋能”,是指技术向政府进行赋能,包括数字技术提升政府的信息汲取能力、监督考核能力、市场监管能力、精准决策能力、民意回应能力等。而所谓“技术赋权”,是指技术向社会的赋权,它通过集体行动逻辑的改变、网络舆情的监督等对政府公权力的运行形成有效制约。可以说,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政府数字化转型通过“技术赋能”和“技术赋权”的双向互动,为数字政府的概念赋予了四方面的理论意涵——
一是新型的民情民意表达机制。时下数字政府的快速发展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发挥出民情民意表达的重要功能,并且这是一种跨地域、跨层级、跨领域的直接民意表达,也就成为传统民意表达渠道的重要补充。二是新型的社会风险感知机制。大规模基于民意数据汇聚,就可以从整体上分析、诊断、预测不同颗粒、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社会风险,从而精准把控社会治理中的关键风险点、矛盾集中点和问题爆发点。三是智能化决策辅助机制。政府数字化转型改变传统基于社会调研或案例分析的政府决策方法,借助民意大数据的深度挖掘和精准预测,大大提升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的同时,也使传统事后应急式社会治理,向事中实时动态的社会治理和实现预防式社会治理转变。四是精准化民意回应机制。政府数字化转型恰会大大提升民意回应机构的回应质量,从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粗放式”“被动式”“标准化”的民意回应变成“精准式”“主动式”“个性化”的民意回应。
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深层问题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中国数字政府如火如荼的建设过程中,也逐渐浮现出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数据整合整体性要求与科层条块碎片化之间的矛盾。科层条块部门间由于利益、制度、观念、编制、标准等原因,往往难以实现数据的打通、共享和整合,这相当程度上阻碍了数字政府功能的实现。例如,我们在基层调研发现,政府机关本可以一套系统垂直到底的软件系统,在科层纵向间就会形成多次重复性数据录入。与此同时,从横向看,公安、工商、质检、食药监、网格、党建等部门间的数据也难以打通。于是,碎片化的科层条块部门延伸到基层,就会形成多套重复性的软件系统和多次重复性数据录入,不但没有给基层减压,反而大大加重了基层负担。
第二,刚性技术载体与柔性体制机制深度融合之间的矛盾。从我们的一线调研看,数字政府的技术载体与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经常出现“两张皮”的情况,导致数字技术和科层业务间相互脱离、相互冲突、相互羁绊等问题,严重制约数字政府治理效能的发挥。比如,不少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均是在未进行底层权责清单梳理和业务流程理顺的情况下,甚至在组织权力和政策法规相互打架的情况下,贸然引入软件公司兜售的软件产品,刚性的技术载体并不能很好地嵌入柔性的体制机制内部,于是出现部门间借助软件系统进行推诿扯皮、规避责任、弄虚作假、形式主义等新问题。换句话说,柔性体制机制是第一位的,刚性技术载体是第二位的,前者决定了数字政府建设的效能,后者仅仅是前者的“润滑剂”,前者本就存在问题的情况下,贸然引入后者,只能使问题更严重。
第三,数字政府建设政府供给与公众需求之间的矛盾。数字政府建设往往是以政府供给为中心的,而不是以公众需求为中心,少数官员试图借助数字政府创新的形式,创造出、博取到或塑造出其个人职业晋升的政绩筹码,而不是站在公众需求的视角,或者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视角,系统提升公众接触或使用数字政府应用过程的便利性、易用性、满意度或信任度等问题。许多耗资巨大的数字政府工程变成了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包括“僵尸网站”“僵尸微博”“僵尸App”“僵尸热线”等。同时,被官员个人政绩最大化目标捕获的同时,还可能被软件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捕获,某些软件公司,借助技术、资本等壁垒优势,大量提供实用价值不足、多次重复建设、使用效率低下的软件产品,也会使数字政府建设更多偏向官员政绩,而偏离公众需求。
第四,软硬件技术过载与数据红利释放不足之间的矛盾。时至今日,中国政府数字化转型已经从软硬件建设为主的第一阶段,整体跃入以数据红利释放为主的第二阶段。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各地数字政府建设依然是重在软硬件建设,而不是数据红利的释放,其原因,一方面是转型的难度。由于技术壁垒、人员认知、市场不足等因素的限制,各地往往很难实现释放数据红利赋能国家治理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激励的偏向。在官员政绩导向、软件公司利润导向等的刺激下,许多地方政府更乐意建设新的数字政府软硬件工程,而不是去激活和用好数据。
中国数字政府建设的未来发展之路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数字政府建设需要深度反思自己的发展路径,瞄准自己的发展定位,根据我国数字政府发展的特殊历史阶段,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各地政府实际的政府数字化转型之路。
第一,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面临科层条块碎片化、体制机制难融合、官员激励偏向、数据红利释放不足等深层次矛盾问题的时候,需要发挥我党的领导作用,通过“自上而下”的宏观顶层设计和政治战略规划,充分调动条块间、部门间、层级间的积极主动性,通过“一把手负责制”“临时领导小组”“政治动员教育”“绩效考核验收”等形式,集中力量破解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的深层问题。
第二,要制定明确战略规划。数字政府建设是一项系统而专业的工程,首先,这就需要制定长远战略规划,做好宏观顶层设计,明确发展目标。其次,需要更加明晰当下中国数字政府发展的战略定位。总体上看,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已经从软硬件建设时期,过渡到释放数据红利赋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时期,这就需要从国家政策层面予以更多扶持,尤其是通过明晰数据产权、健全数据要素市场、探索数据授权运营等形式,推动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的相互助力和互动协调发展,建构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智能化社会治理结构。
第三,要深入推进数字政府法治建设。一方面,柔性体制机制是刚性技术载体介入的依据,在体制机制层面的改革或制度创新恰恰是引入软件系统的依据,只不过是用“软件即代码”的形式,将新产生的制度用软件系统予以巩固;另一方面,软件系统中累积的数据,恰恰成为暴露社会治理问题,尤其是体制机制漏洞的风向标或指南针,要通过及时立法的形式,破解大数据分析中暴露出的历史性、累积性、积压性治理难题,通过弥补制度漏洞的形式,深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者系山东大学法学院(威海)研究员,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责任编辑: 崔凯铭 张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