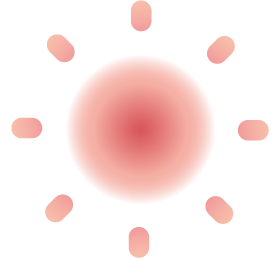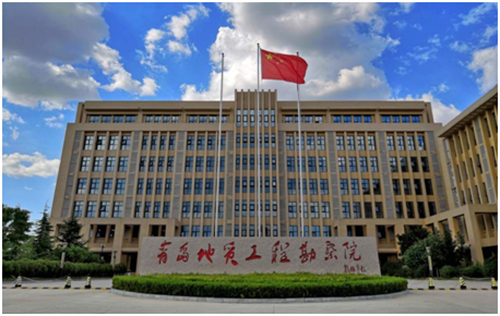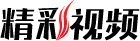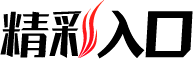【与时舒卷】生命的质地——读谭宗远《雅居日记》
2021-02-21 12:23:46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 张期鹏
新正大月,初五,我从老家一回济南,就收到了一大抱网购的书刊。在这摞书刊中,我看到了北京谭宗远兄的这本《雅居日记》,一下子被它迷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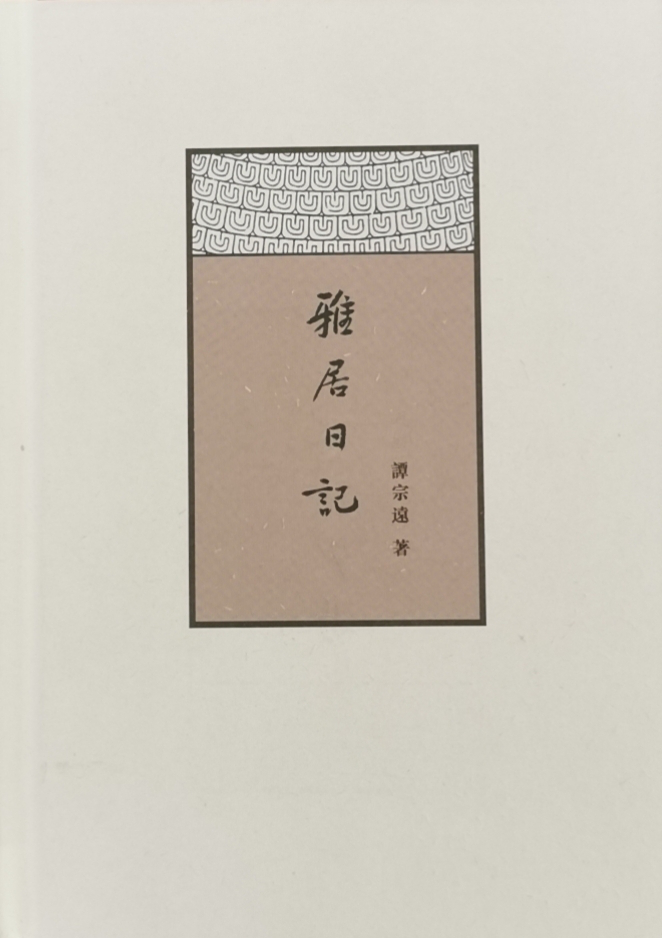
《雅居日记》,谭宗远著
芳草地书屋2020年11月出版
说起谭宗远,大概很多人并不知晓。在全国民间读书界,他可是个鼎鼎有名的人物。我与他是通过文字认识的,仅有过一面之缘。那是翻译家高莽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我去北京就我编写的《高莽书影录》请教高老,顺便到他供职的朝阳区文化馆去拜访。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他已从文化馆退休,正被返聘回来编那本他已经编了多年的《芳草地》。一听我来,他顾不得休息,专门从家里跑到编辑部等我,还送我很多书刊。他是回族,又在斋月,白天封斋不吃饭,我们就没有把盏畅聊,但他依然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是个单纯热情、做事痛快的书生。一般书生都有些黏黏糊糊、婆婆妈妈,宗远兄不,说话干脆,赠书也很大方,让我喜欢。以后我们联系很少,因为大家都不愿闲扯,对请安问好一类的客套也很讨厌,即使电话、微信方便,也不想浪费时间。偶有几次,是我写了文章发他,问他可否在《芳草地》上用一下,每次他都痛快地说“行”。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人。
这样一个人是如何养成的呢?我有时不免纳闷,偶尔也猜想一番。但因与他还没熟到无话不谈的地步,纵有疑惑也不便打听,所以一直疑惑至今。现在有了这样一本《雅居日记》,初步解开了我心中的谜团。
这部日记是2020年11月由芳草地书屋出版的精装本,36开,自印本。虽是自印,但设计、装帧、印制都很专业。看看介绍,书只印了200册。我这本就是宝贵的二百分之一了。
细细翻看这本书,发现这是他整理的1985年全年日记和1986年日记的一部分。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段的日记,是因为这两年对他非常重要。他在自序中写道:“人的一生再平凡,也总有决定命运的转折点。八五年是我面临人生转折的关键一年,这年我在努力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关于高考,我曾有过一次伤心的经历,有机会再说),希图借此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在学历还没有到手时,我就已经在寻找机会,并屡屡受挫。感谢朝阳区文化局和文化馆,以温暖的胸襟接纳了我,让我在八六年刚刚取得大专学历,就迅即实现了人生转折。因此,我附录了八六年部分日记,给这次转折留下一个较为完整的记录。”
在进入朝阳区文化馆前,宗远兄在北京市半导体器件四厂工作。从他的日记和本书跋中,我约略知道了一些他的经历:1952年4月7日生于北京,14岁念初一,1968年初中毕业。后到内蒙古,1976年2月从内蒙古兵团病退回京,11月1日进入北京市半导体器件四厂(当时叫东城区半导体器件一厂),先烧锅炉,后调行政科搞外勤采买,又调供应科材料库当库工三个月,最后在供应科管材料供应。至1986年9月17日到朝阳区文化馆上班,他在这个厂待了有10年时间。
对于自序中不愿提及的高考,他在跋中也有了清楚的交代:“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二十五岁,按说可以报考,但我有两怕,一怕底子薄,考不上;二怕大学毕业后分到外地工作(我刚从外地调回北京,真怕再出去了),就没有报。高考结束后,我看到了试卷,除了数学一窍不通外,语文、历史、地理等都觉得不难,就有了参加下一年高考的想法。”于是他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历史、地理、政治都超过了六十分,语文居然考了个九十一点五的高分,总分二百九十三分”;数学是零分,因为他觉得不会,干脆放弃未考。可是那一年录取分数线定在了300分,他差了7分。他“心里反复念叨着,不禁悲从中来,恨不得拿头往墙上撞”。
他受人指点去找东城区招生办公室,希望能凭语文单科成绩高被破格录取,可招办的人说没有这方面的政策,还责问他:“你为什么不考数学?有理数无理数你总会吧,怎么也能拿七分呀。”最后还说:“真太可惜了,这次北京语文考九十分以上的也就四十来人。”这更增添了他的懊恼。他给北京市领导写信反映自己的状况,未见回音。不过,因为高考成绩不错,他从烧锅炉调到行政科担任后勤采买,成了行政人员,也算不幸之中的“小幸”。1979年高考又要到了,正在他跃跃欲试的时候,新规出台,不再招收25岁以上的考生。大学校门在他面前彻底关闭了。
那是一个靠考大学、考中专,靠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时代之火撩动着每一个青年人的心,每个人都不会轻言放弃。失去了考大学机会的宗远兄,进入了东城区开办的一所业余大学学习。那时上业大需单位批准,宗远兄记得,厂里主管此事的郭淑芬老师很快同意了,他经过考试被编入了中文一班。批准他上学的郭淑芬,是诗人、东方艺术史研究专家常任侠先生的夫人。
遗憾的是,因为1980年5月儿子降生,家庭负担骤增,他实在无力坚持白天上班、晚上上课的疲劳奔波,只好放弃了业大学习。直到1982年得到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消息后,才又重新燃起了希望的火苗。3月29日,他办理了自考准考证,“第一门大学语文,八二年上半年考,通过。八三年考政经、写作、文学概论,只写作通过,那两门被击落。八四年重考文学概论和政经通过,又考了中共党史和现代汉语,党史通过,现代汉语落马”。就这样一直到了1985年,也就是《雅居日记》中所写的年份。我们在这年日记中,看到宗远兄最热望、最纠结、最痛苦的就是自学考试。他在元旦那天就定下目标:“今年努力争取全部拿下。这是全年的奋斗目标。”可要拿下谈何容易。因此,1985年注定了是宗远兄无比艰辛的一年。
1985年1月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一直在看中国文学史和作品选,还有大部分没有看,四月中旬就要考试。《现代汉语》准备在考前一个多月看。”1月23日又写道:“距考试还有将近三个月,该加加班了。晚上在台灯前看书两小时,就从今天开始努力吧。”3月14日写道:“距考试还有二十天,但脑子里仍觉茫然,空无所有。不管结果怎样,这些日子还得努力一下。”3月20日写道:“无心看功课,还有十几天就要考试了,如何是好。”3月16日写道:“取回准考证。下月十四日考中国文学史,二十一日考现代汉语。”4月7日生日那天写道:“三十三岁生日。回思以往,平平凡凡,唯一可宽慰的,是读过几本书,写过几篇小文,去过几个地方,并且正在向大专进军。但三十三岁已是人生的一半,实在不甘心如此平庸地活着,老想做点什么。我希望早日拿下大专文凭,结束这马拉松式的考试,然后专心看点书,写点文章,最迟明年年底前实现这个愿望。”4月9日写道:“距考试还有四天,加把劲,休管成败如何。”4月11日写道:“为应考未上班,在家看书。”4月12日写道:“休息。温文学史一二册毕,始看第三册。”4月13日写道:“温书,感觉记性很坏,看过就忘,加上感冒,怕考不好。”4月14日写道:“下午参加中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考试,感觉最好也就是将及格。”4月15日写道:“本周考现代汉语,又是一番苦斗。今天开始看书,真乏味,怎么也记不住。自学考试苦不堪言,我厌倦了。”4月19日写道:“右眼红且痛,是结膜炎,全天没怎么看书,考试真成问题了。”4月20日写道:“眼疾见轻,还是决定考。书来不及细读,粗看几遍而已,估计很难通过。”4月21日写道:“下午考现代汉语。昨天和今天上午看了三遍书(跳读重点),感觉似乎能及格。但愿及格。”自学过程的艰辛,考前的焦虑,考后的忐忑不安和微渺希望,都在这些简略、平实的文字中表露无遗。6月7日,考试结果出来,现代汉语通过了,中国文学史及作品选却差了8分。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咬紧牙关再拼下半年。就这样,他在10月又参加了古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史及作品选考试,均通过。1986年4月参加了中国文学史及作品选考试,得到了84分的高分。至此,他的大专自学考试课程全部结束,终于成了一名大专毕业生。
当时,成为一名大专毕业生对一个青年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他才能进入“人才”行列,才能走出工厂,去实现自己的梦想。1986年6月29日,为了庆贺拿到学历,他特意请母亲和兄、姐全家到家里吃了一顿午饭,“妻采购、做饭一手包办,可感”。他们一家人的笑语欢声、其乐融融的情景,我们今天似乎都可以感受到。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通过自学考试作为宗远兄实现命运转折的条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从他的日记中看到,自学考试只是这个青年努力奋斗的一个方面,伴随他的青春旅程的最重要的还是阅读。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阅读的黄金时代,宗远兄无疑是那个时代较为突出的一个。在他的日记中,我们看到的几乎是无处不有的购书记录。我们不妨拿他1985年1月的日记,来看看其购书的密集程度:1月3日,“购《孩子,别回头》《马丁什么也没偷》《翘尾巴的火鸡》《三个小流浪儿》四本外国儿童小说,另购清代笔记两本,共花二元零一分。小说将来给儿子”;1月4日,“购《世界文学》八四年第六期、《外国文学》八四年第十二期”;1月7日,“购《文史知识》八四年十二月号”;1月10日,“购《外国文艺》八四年第五期和托翁《高加索的俘虏》二书”;1月11日,“购《‘月光号’沉没》等三本小说,花一元二角九分”;1月12日,“购特价书《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七角五分。……另购安徒生童话全集三本(一元二角四分)。此全集共十六册,凑齐约需七元左右”;1月17日,“买《散文选刊》八四年第三期”;1月19日,“买大仲马《三个火枪手》上册(五角)。又买了《陈璧诗文残稿笺证》。后书是田园诗派作品,内容清新可喜”;1月21日,“花六角钱买了两本八三年的《外国文学》,读了其中两篇小说。”;1月22日,“购《郁达夫散文选集》”;1月25日,“买《书林》一本。过去一直买《读书》,现《读书》已涨到五角五分一本,故改买了这本《书林》(双月刊,三角六分一本)”;1月26日,“购旧书若干本,花一元多”。其他各月情况,大体也是如此。
这一年,他代表厂里出差特别多,先后到过鞍山、烟台、蓬莱、青岛、保定、常州、镇江、洛阳、无锡、天津等地,每到一地,只要有机会他都不忘买书。在青岛,他“顺道去中山路,在古旧书店买了几本旧书”,并在入住的黄海酒店“买了一本纪昀(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离开前还“到古旧书店和栈桥,向这两地告别”;在天津,他“午饭后,到和平街新华书店和劝业场古籍书店,买新旧书各一本”;乘火车从无锡到戚墅堰,“等车时在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的自传体小说《窗边的阿彻》,在火车上读了前几章。确实好,有儿童情趣,笔调也朴实优美”。他年终统计,全年购书多达160本。这对当年一个收入不高的工人来说,应该是个很大的数目。这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和文化书刊,慢慢拓展了他的视野,滋养了他的性情,铸成了他的梦想。蜜蜂采蜜,终有一天会酿造出甘甜的。
因为买书,他对图书价格特别敏感。1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因木材涨价,今年书价也相应提高,幅度不小,估计这个势头要持续多年,故近来多买了几本书,以防将来再提价。”因为注重纯粹的文学和文化阅读,他对一些不良出版现象也表示了忧虑和愤慨。1月1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东单邮局前看到一群人抢购小报。小报内容无非情杀、奇案之类,每份竟卖三毛多钱。在纸张金贵的今天,印行这类玩意儿,纯属误国害人。”12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电视播‘南腔北调大会唱’,唱京剧用电子乐伴奏,真是胡来。幸亏这些人还没把京胡、月琴革掉。报上还有人为之喝彩,地道的捧臭脚。又,手拿麦克风唱京戏也不伦不类。”同时,因为对于文学和文化的关注,他对那些文学艺术界名家也特别留意。在1985年日记中,他就记下了演员韩非、翁美玲,戏曲文学史家赵景深,红学研究专家王昆仑,作家白危、张天翼、华山,山水画家钱松喦,《长征组歌》的作者萧华等故去的消息。
除了买书、读书,宗远兄也在不断地写作、投稿。也许因为他的长兄谭宗尧是演员的缘故,他那时特别喜欢看电影、电视剧、话剧,投稿中既有读书所感,也有不少影评、剧评。比如他说:1月4日,“收到《电影介绍》稿费七元二角”;1月18日,“写了看电视剧《吉祥胡同甲五号》的文章,交莱莱,托他转《戏剧电影报》,不知能否发表”;1月27日,“去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写的《一幅反奴役的历史画卷——浅谈<女奴>》,发表在今年第二期《新观察》上,只结尾有改动,其他文字没动,署了四个人的名,实出自我手”;1月30日,“晚上重写《读了<小银和我>》,成一千二百字,子夜抄毕,试投《博览群书》杂志,不知能用否”;2月12日,“写完《门钉肉饼》一文,试投广州《随笔》双月刊”,等等。这些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很多,其中有些文章发表,有些则被退稿或石沉大海。据他年终计算,1985年共发表文章5篇。看起来数量不多,但对一个业余作者来说,也算收获很大了。
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都构成了宗远兄生命的质地。这也滋养了他纯正的心灵,培育了他的心地坦荡和正直无私。他在1985年4月8日的日记中记载:“常州来人,带来一辆金狮自行车,说是送我的,坚辞不受,给了来人一百八十六元,把车买下。”他在厂里管材料供应,经常去购买一些黄金等贵重金属,但他一分一毫也不会染指。他虽然特别渴望离开工厂,到一个文化单位发挥自己所长,但不论是设法联系到《曲艺》杂志、《中国妇女报》当编辑,还是最终去朝阳区文化馆工作,他主要都是凭借自己发表作品和自学考试取得大专文凭的实力,而不是其他。1986年3月28日,在调往朝阳区文化馆遇到障碍,一位姓张的女馆长坚持要看他的自学考试单科结业证书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态度:下周一找她时,先问她感觉我能力如何,有无希望调来,如果回答接近否定,就不必让她看证明了,将材料取回,此事一笔勾销。我不会低声下气求人,也讨厌人家在我面前摆出一副傲慢的臭架子。”3月30日又写道:“晋刘琨《重赠卢湛》诗有‘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二句,我可对号入座。念我长生至今,懦弱有余而‘钢性’不足,事事随方就圆,处处委曲求全。虽有一定的主见,怎奈各方压力阻力太大,只好放弃或改变。即如目前,事事不顺心,想调动工作,人家却以体制、政治面目、是否干部、有无才干等等来要挟你,我好比一件商品,任人挑拣,说三道四,一处不中意,便扔在一边。我本不是‘百炼钢’,经此折腾,简直快变成软面条、鼻涕虫了。”但即使在这样郁闷之时,他也没有失掉自信,他在4月7日自己34岁生日那天写道:“三十四岁生日。深感光阴荏苒,成绩微小。拿下文凭后,一定大干一场,虽难成大器,也要无愧于心。”后来宗远兄知道,他在日记中啧有烦言的那位张馆长,其实“很有工作能力,性格直爽,精明干练,业务很强,五十年代风靡全国的《青年友谊圆舞曲》集体舞,据说就是她编创的”;宗远兄调去后,她对他也一直很器重。宗远兄说,自己那时是过于敏感了。但正是这份敏感,给了他强烈的自尊与自信。这对一个人的成长来说,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1986年9月17日上午,他正式到朝阳区文化局报到,下午即到文化馆开会,接受朝阳区第三届群众文化节开幕式的任务,充当舞台工作人员。那天下午,他还和文学组未来的同事见了面。“文学组是半日坐班,负责朝阳文学创作协会六十多名会员的创作、辅导,组织讲座,安排讨论,并编一份《芳草地》小报”。
从此,一段新的生活开始了。他当时绝不会想到,他在这里居然一直待到退休,退休后又返聘编刊。至这本《雅居日记》印行时,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34年。在这30多年间,他也沿着自己当年渴望的那条道路不断前行,买书、读书、写作、编刊,为朝阳以及朝阳之外的文化人服务,渐渐也把自己锻造成了一个民间文化人。
这就不免要说到这本《雅居日记》书名的来历。宗远兄在自序中说,“雅居”者,不是指“居所优雅”,而是因为他当时所居住的大雅宝胡同有一个“雅”字,这个胡同里也住了很多“雅人”:“我住在九号院,东边紧邻的是二号院,两扇大门,门外有几棵老槐树。这里住过孙伏园、张静庐、徐放、米谷等大名人,我在的时候,漫画家毕克官还住在里面,我们时常在胡同的公厕里碰面。二号院往东不数武是甲二号院,中央美院宿舍,荟萃了一群美术巨子——董希文、李可染、李苦禅、黄永玉等。我在的时候,别人我不清楚,周令钊、侯一民两家确还没有搬走。好多年后,我陪周令钊先生的女公子周容老师(执教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回过一次甲二号,有幸见到了董希文的遗孀,一位白发老太太。我们走进她家,没有待住就出来了,但我内心确曾对那间屋中充满了景仰之情,我知道这位油画大师生前就在这里起居,房间里应该还留存着他的生命气息。屋里的家具摆设已经过时,但有个不大的镜框却熠熠生辉——镜框里摆放着一张董希文的自画像。”我想,在宗远兄的生命底色中,也许就有这些名家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很想看到他进入朝阳区文化馆后30多年间的日记,那里面很可能蕴藏着一些生动鲜活的“朝阳文化史料”呢。
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一个令人回味、神往的“黄金时代”,宗远兄在那个时代用自己的执着、坚韧涂写了浑厚的生命底色,也为自己的未来奠基。而今,那样的时代已经远去,一去不返,我们如何面对今天,实在是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荒废了今天的岁月,将来回忆起来会不会感到后悔呢?想想似乎也不必担心,因为正如宗远兄所说,人是健忘的动物,很多东西不多时候就归入忘川了。是这些日记让他在回忆往事时不再一片空白。现在的人忙得脚不沾地,大概已经很少有人记什么日记,甚至连回味一下昨天的工夫都没有了。
我们不再回忆过去,我们已将很多事情归入忘川。那么,我们又如何走向未来呢?

谭宗远,1952年4 月生于北京。回族。北京作协会员,中国作协会员。曾担任中宣部第九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奖”戏剧评委。著有《卧读偶拾》《灯心草》《文人影》等随笔集。现为北京民刊《芳草地》杂志主编。
责任编辑: 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