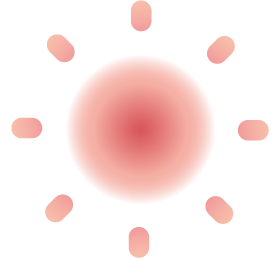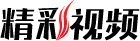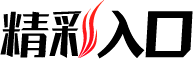生命站台的点灯人
2023-04-05 10:09:08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柯含
清明的雨,每一滴都带着淡淡的思绪,缄默而疏离地洗涤着城市的每一处角落。清明的阴郁和寂寥,与万物复苏的仲春缠绵交融着,我在这样特别的时节,这样的雨天小心旋开半盏台灯,任笔尖沉默地流淌,淌出我酝酿已久的,她的故事。
她是我的祖母,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坚强的人。自我记事起,她便日日为我们的小家庭做着无微不至的后勤工作。我从前时常偷着乐:因为有祖母的奉献,父母得以安心工作,少些柴米油盐的操劳;我也算拥有一个充满陪伴的童年,安心读书上大学,我们小家庭的日子是多么地简单而快乐!一年又一年,时光长河中家事的变迁,却让我慢慢感受到,祖母从纯粹的快乐,变成仅存的乐观,她的开朗成了咬牙强撑的坚强。
听闻祖母曾经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三世同堂,人丁兴旺。而在她二十岁的那一年,家里的三个长辈在一年之内匆匆离开了她。作为姐姐嫁人后家中留下的长女,我的祖母一边做着民办教师,一边耕耘着家中的土地。她放弃了学业,忍受着饥馑,将弟弟妹妹抚养成人,直到后来彼此有了安定的生活。我见过祖母曾经的学生,也听过现任大学物理教授的舅公提起往事,在那个年代,祖母一定是最辛苦的姐姐,也一定是最称职的老师,她用瘦弱的双手寻觅着困苦生活中远方的微光,也牺牲了自己为村里的孩子们照亮求知的道路。

在父亲和我童年的印象中,祖母一直是一个精干的“当家主母”。祖父沉默寡言,行动迟缓,因此经常受到急性子祖母的“疯狂输出”式谴责。我曾傻傻问祖母:“你到底爱不爱我爷爷?”老两口总是给对方一个大大的白眼,随后笑而不语。那年,祖父得了绝症,日常的拌嘴变成轻声地关切,房间内曾经的调侃多了些呻吟与叹息……直到那天,祖父走了,我从学校匆匆赶回家磕头送行。我打开祖母的房门,祖母一个人在黑暗的房间里埋头趴在床的中央,听见门响后,不抬头地招手示意我离开。自祖父离开那天起,祖母变了,我常听到房间内有隐隐约约的啜泣声,还有相册膜纸被反复翻阅的沙沙声,特别是调皮的我,反复惹怒祖母想着“肯定要挨打了”以后,居然看到祖母转过身,无助地掩面而泣。十几年前的事情啊,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祖母不曾回答我爱与不爱,可我分明得到了那个问题的答案——祖父在陪伴了祖母40年后悄然离开,如果不是爱,昔日的责骂怎会化作思念的云烟;如果不是爱,又怎会常于泪光中苦苦留恋。
天真的孩子沉溺于生活的简单,我本以为祖父离开了,祖母慢慢释然,加之堂叔们纷纷成家,姑姑又新生了小宝宝,父母工作一帆风顺,家中的生活渐渐丰富了起来,接踵而来的快乐将抹平那个悲伤的夏天,让祖母颐养天年。谁知一次运动会前,祖母正与母亲分享自己做的奇怪梦,母亲“连哄带骗”安顿下祖母后,悄悄地进入我的房间,锁上房门告诉我:“你姑姑病倒了,我不知道还能瞒多久……”我实在语塞,因为祖母十分相信她的直觉,时不时问我姑姑的事,在一次又一次搪塞后,母亲终于意识到祖母的执着,将这个消息告诉了祖母。祖母只是点点头,第二天便收拾行李返回老家,照顾病中的姑姑和年幼的小弟弟。姑姑的病反复无常,一次次陷入危机又一次次悬崖勒马,在此期间祖母不顾自己日渐衰老的身体,始终忙前忙后照顾着姑姑,直到姑姑做了手术,降低了风险,才暂时安下一颗心。几年过去了,我每次见到谈笑风生的姑姑,就觉得姑姑似乎是最幸运的人,祖母的照顾有了很大的起色。
三年前的11月,我在大学高数课上昏昏欲睡时,父亲发来信息:“回来吧,你姑姑不行了。”我扔下书本冲出教室,眼泪在初冬的北风里被吹散成雾,一路上我精神恍惚,脑海里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生活要这样对待我奶奶?为什么一定要是奶奶?为什么…”我期待着几乎不存在的奇迹,那一晚我还是回家了,祖母却表现的异常平静。她哄睡第二天要上学的弟弟,把我的行李拿进房间,轻声说:“饿了吧,吃点罐头,姑姑做的……”我看着她,她不看我,我捧着罐头,刚要呷一口快要溢出的糖水,她突然拿走罐头,分一半到碗里,“你还是只吃一半吧,给弟弟留一半,他可能再也吃不到了……”祖母出奇的平静让我眼泪夺眶而出,我哽咽着叫着:“奶奶,奶奶…”祖母却留下一句“吃完睡吧,明天再说”便转身进了房间。我搂着姑姑的棉袄辗转了一夜,房外祖母的灯光也一直亮着,三个房间,四个人,心照不宣却共同沉默。
姑姑还是离开了,作为成年的孩子,我必须搀扶祖母去为姑姑送行。仪式全程,祖母平静地回应着每一个人的吊唁,点着头说自己很好,就连看到姑姑的遗容时也抹去眼泪,坚定地说:“行了,走吧!”而当她踏上回程的车,与众人挥手告别,积压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她在车上像个失去糖的孩子那样放声大哭。我的心绞痛,命运的玩笑还是彻头彻尾地开起来了,我竟不知她此刻是恨,是痛,还是悔。
父亲说,人是要向前看的。可是姑姑走后这些年,祖母越来越像个孩子,她变得十分激进与激动:她曾固执地呆在老家,恨铁不成钢地教训着不爱念书的弟弟;生气了就大哭,不顾父母劝阻地刷着手机,在好不容易学会的微信群聊里转发着一条又一条稀奇古怪的消息;我的压岁钱骤然变得十分丰厚,连父母都时而费解,问道:“您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面对祖母如今的性子,我有一刹那突然明白,有一种坚强叫逞强,那种坚强的背后,是何其剧烈的疼痛,唯有苦苦挖掘着些许的期待,更为倾心地为别人而付出,才能暂时地忘记,寻一份心安。
那日我从房间出来,看见一夜无眠的祖母在餐桌上落寞地择着韭菜,眼都不抬地苦笑一声:“我又失去一个亲人了…”我虽不十分了解那个亲人是谁,可是祖母的声音分明再无哽咽,只有麻木中带着丝丝遗憾。我没有说话,只是抚着祖母的后背,像我赖在她床上她安抚我的那样。祖母的老花镜反射着餐厅的灯光,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一个站台,祖母此刻孤身一人站在那里,目送着一个又一个旅人的离去。这些离开的旅人中,有她的父母,她的伴侣,她的女儿,她的一个又一个家人和朋友……这些旅人都完整的度过了属于他们的旅程,虽有遗憾,但在旅程的最后一个路口,都收到了祖母全心全意的关照和发自内心的祝福。微光中,我看见他们向祖母挥手致意,随后走向永恒的黑暗。而祖母只是静默着,原地点着灯,无声地目送,沉默地惜别。送别不是桃花流水、长亭古道,纪念也非歌吟行畔,口口相传,而是夜深时,生命站台边,唯祖母一人,心中悄然落雪。

又是一年清明,我第一次感受到“断魂”的内涵所在。清明属于追忆与祭奠,我此刻与祖母将心比心,竟发现最难过的,莫过于满腔感慨却一时不知该祭奠谁,追忆谁,只得默默地将祝福洒在雨中,化作一首离歌,无词却满是感念。此刻,我想每个人都在生命的旅途中奔忙,只愿我们都能待人以慈悲,做他人生命站台的点灯人;也愿终有一天,在不得不栖息的终点站,有一人,点着灯守在无底黑暗前,与君唱一首送别。
(作者为南开大学学生)
责任编辑: 蔡继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