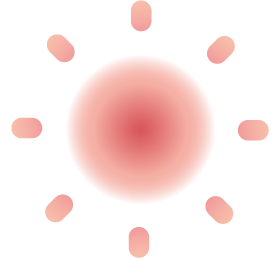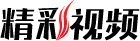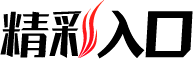大家‖像汪曾祺一样生活
2021-05-16 16:34:35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 王 干
汪老虽已去世24年了,但仿佛还在世一样,影响很大。00后的学生都非常喜欢汪曾祺,以至于有“开口不谈汪曾祺,纵读诗书也枉然”的说法。
曾有调查显示,除了鲁迅之外,作品被付印出版次数最多的就是汪曾祺。202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了一套汪曾祺全集,价格偏贵,一套700多元。居然加印了三次。原本出版社认为8000套已经封顶了,因为全集除了研究者和粉丝以外,很少有读者购买,现在却三次加印,卖了两万多册,可见其魅力。我曾邀请上海大学的郜元宝教授写一篇关于汪曾祺《星期天》的介绍文章,郜元宝看完《星期天》后惊呼“这是一个伟大的杰作”,结果最后写了一篇16000字的文章。汪老这篇小说总共才8000字,他写了16000字的评论文章,尚觉不过瘾。
一般都认为汪先生受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影响,但是我研究的时候发现汪曾祺跟《史记》的关系更深,他写的人物都是真人,部分健在可考证,采用本纪跟世家的写法。他偏爱古代笔记小说中畸形的人,有异秉的人。比如陈小手是男性,但他的职业是接生婆,也就是男妇产科医生,又比如陈四踩高跷走了30里路去县城的故事,都非常奇异。

汪曾祺最有名的作品比如《大淖记事》《受戒》,散文《端午的鸭蛋》,还有60后比较熟悉的《沙家浜》,里面经典的唱词都是汪先生写的,如我们现在还用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非常符合现代人的社会交际,表面是一个茶馆的事,实际指人情冷暖。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愿意看汪先生的文章?汪先生有地道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他不直接写中国人、中国文化,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普通人,都是老百姓。汪先生曾在西南联大求学,师从沈从文。沈从文当时教授创意写作课。汪先生向沈先生请教小说怎么写,沈先生的回答是“贴着人物写”。可以扩展为首先要贴着人物性格来写,第二要贴着人物的命运写,第三要贴着人物的灵魂写。《陈小手》就是“贴着人物写”的经典作品。故事简短但很有意味,男妇产科医生陈小手长着一双非常小的手,专门接疑难杂症。产妇难产往往性命不保,县里的保安团长的三姨太太难产,为了保住产妇不得不请来了陈小手。陈小手一到,母子平安,团长请他喝了酒并给了二十大洋。陈小手酒足饭饱后,待他骑上大白马,团长把枪举了起来,这是欧·亨利式的结尾。最精彩的是团长说了一句“奶奶的,我的女人也能让你摸来摸去的”,作品的最后汪曾祺又写了7个字,“团长感到很委屈”。这是神来之笔,我们看完故事一般都觉得愤怒,陈小手救人却被杀,可团长是真的觉得委屈,这就写出了一个人物的灵魂,那时候的女人并不是人,而是男性的附庸财产。汪曾祺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特点,人物灵魂是病态的,心理阴暗。这篇小说并不是简单的谴责和批判,他写出了团长的委屈。这个委屈背后,是男权社会的基本人性的扭曲,可以说这是两性不平等带来的男性的“变异”。汪曾祺笔下几乎没有坏人,他笔下的团长的心理,是“贴着人物写”的典型。

汪曾祺写的大都是吃吃喝喝市井生活,是充斥人间烟火气的东西,但他做到了“六个打通”——打通了现当代文学、古今文学、中西文化、雅俗文化、南北文化以及“尘界”与“天界”。
20世纪40年代,他就加入了京派的创作,当时创作的《鸡鸭名家》等已成为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能把新中国成立前后两个时代连起来并写出伟大作品的,汪曾祺是第一位,他是把现代文学的精神、文脉贯穿到了当代,将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无缝对接。
汪先生对古代文学特别熟悉,写的文章里面我们能感到一种古韵,白话文里有唐诗宋词的味道,这是汪先生从小的家庭教育所致,他精通古典文学以及中国书画,对中华文化的传承非常到位。

年轻时的汪曾祺写过一部小说《小学堂的钟声》,是学习英国作家伍尔夫《墙上的斑点》,这是伍尔夫意识流的代表作,他接触了很多西方文学,特别喜欢西班牙的阿索林。纯粹的传统文化之外,汪曾祺需要通过西方文化来重新关照中国文化,用西方文学的眼光和视野来看中国的生活。20世纪40年代西方意识流刚刚传入,汪曾祺就接触到了。汪先生是一座桥,是连接古今文学、中西文学、现当代文学的一座桥梁。
打通古今、中外、现当代的作家有钱钟书、沈从文、鲁迅、胡适等,但他们都偏雅文化,知识分子喜欢。汪曾祺的作品不仅是雅文化,同样是民间文化,他的作品非常接地气,他与作品中的人物没有隔阂。当年工作分配,汪曾祺听从老舍安排,很高兴地去了“说说唱唱”(民间文学)工作,和赵树理合作,汪先生借此看了几万首民歌、很多民间故事传说。后来汪先生去河北生活了七八年,他的写作是深入生活后的写作,是身心都沉浸在底层民间的结果,所以他小说里有大量的民俗描写。赵树理是大俗大雅,汪曾祺是大雅大俗。后来汪先生去京剧院做编剧,中国的戏曲也是语言的巅峰,《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唱词非常了不得。

汪先生最早在高邮生活,中学时在江阴,大学时代在昆明,后至上海工作,又调动至北京故宫、北京文联、民间文学协会,后被打成右派到河北工作。汪先生的生活轨迹是不停变化的,他笔下的美食,有淮扬菜、北京菜、云南菜、内蒙古菜,汪先生深入接触了南北文化并将其打通。《七里茶坊》写冬天劳作,几个人一边敲着冻成冰块的粪坑,一边回忆着昆明的美酒,充满生活的乐趣。没有南北文化的交融就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汪曾祺还打通了“尘界”与“天界”。“尘界”就是日常生活,是我们肉身所栖身的存在;“天界”是指人心,是我们的精神空间。“天界”其实是我们精神的翱翔,是我们心灵的家园,灵魂的栖息所在。而在“尘界”“天界”之间还有个“魔界”,“魔界”是欲望、贪念,我们大多数人是生活在“魔界”里的,关于官场、职场、情场……各种纠结和挣扎。而汪曾祺是“去魔界”的,在这个嘈杂的尘世,我们要学习汪曾祺,在“尘界”里要有“天界”的胸怀、灵魂,在“魔界”中行走、生活,就不会变成“魔鬼”。所以假如你以“天界”的思维来俯瞰“尘界”的芸芸众生,很多事情也就一笑了之了。
汪曾祺曾作自题诗:“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可见,汪曾祺是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的,他的文学思想、人生价值观是为人间“送小温”的。

责任编辑: 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