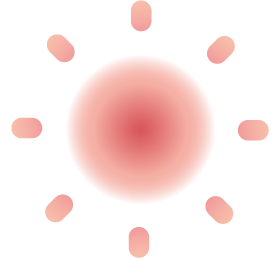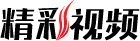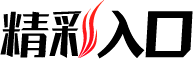文化之窗丨“盗”亦有道
大众日报记者 于国鹏
2023-02-07 17:21:00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1月26日,省京剧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迎新春线上展演季专题展播第九场剧目,其中有一场是《盗仙草》。看到这台戏,不禁想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在京剧中,有很多以“盗”为名创作的剧目,创作者对这些特殊之“盗”,显然并无贬斥之意,而是持肯定甚至是赞赏态度的。这有以“盗”为理由编织故事的原因,里面包含的“事不凝滞,理贵变通”的辩证思维,琢磨起来特别有味道。

直接以“盗”字取名的戏很多,常见的如《盗魂铃》《三盗令》《三盗九龙杯》等;有的是精彩选场,如《白蛇传》中的《盗仙草》,《四郎探母》中的《盗令》,《连环套》中的《盗御马》等。还有的虽非以“盗”命名,但包含这样的情节,如《四进士》中宋士杰之暗中“盗”信;《赵氏孤儿》中,程婴之“盗”婴儿。再比如,《春草闯堂》中相国之女李半月、丫环春草,也是在成功“盗”得相国书信后,在信上动了一番手脚,导致李相国的安排阴差阳错,才让李半月迎来一段如意姻缘。
“盗”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词性,可指盗行,也可指为盗之人。盗,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偷窃,也有的用来指代外来的侵略者、破坏者。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盗”当然是否定的;从法律角度来说,盗是触犯法条的,所以,无论情、理、法,哪方面都不支持“盗”。人们唾弃盗行,也不齿为盗之人。孔子过盗泉,虽渴而不饮,原因是“恶其名也”,足可见人们对“盗”或者为“盗”之人的反感。
在文学创作中,很多作家喜欢围绕“盗”编织故事,因为有这个情节更容易制造冲突和悬念。京剧也不例外。但是,在这些与“盗”有关的剧目中,往往对“盗”有不一样的描述和诠释。在戏里,那些“盗”一般是出于善良、正义的目的,且并未伤害别人。观众对这些特殊之“盗”,尤其是扶正除恶之“盗”,给予了格外的理解和宽容。
以《盗仙草》为例。《盗仙草》是《白蛇传》选场,故事情节大家非常熟悉。许仙听从法海之言,于端阳节劝白素贞饮下雄黄酒。白素贞酒后现出白蛇原形,许仙受惊吓而死。为使许仙复生,白素贞毅然前往昆仑山,欲潜盗灵芝仙草。鹤鹿二仙阻止,白素贞不敌。恰在此时,南极仙翁出现,出于同情赠白素贞以灵芝。白素贞取得仙草,终救活许仙。
《盗仙草》的故事,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就白素贞而言,更是一个充满光彩的女性形象。她敢爱敢恨,喜欢许仙之才貌,并未羞于启齿,而是大胆表达;恨法海之挑拨,则勇于直斥,敢于当面抗争。她对爱情又极为忠贞,平日贤惠持家。为救许仙,她明知到昆仑山盗取仙草困难重重,危险重重,甚至极有可能生命不保,依然义无反顾,怀抱赴死之心前往。这些品行对于一位女性来讲,无疑都是加分项。如此一位女性,又何不令人感佩?
或许有人会问,她为何一定要盗取?光明正大去求取不行吗?还真不行。因为她的身份,决定了她只有盗取一途。她本是修炼成精的白蛇,是一个蛇精,与神仙自然不同。一般说来,神仙代表正义,妖怪代表邪恶,二者正邪不两立。在神仙眼里,她属于妖精,是邪道,是祸害。神仙见了妖怪,是欲除之而后快的。对白素贞而言,如若当面求取,无异于自投罗网,不仅难得仙草,还会误了自身性命。思来想去,她也只能采取冒险“盗取”这个不算办法的办法了。
正因此,白素贞的形象是有一个逐渐演变过程的,由亦正亦邪慢慢被净化为正面形象。最初,明冯梦龙《警世通言》中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写到的白娘子,既有人的贤淑可爱的一面,也有妖的狰狞可怖的一面。至清代,讲述白娘子故事的有弹词《义妖传》,从这个弹词的取名可见,白蛇前面虽然加了个“义”的定语,但仍然着重强调了其“妖”的一面。随着后世不断加工改编,白素贞的形象逐渐净化、正面化。在这个过程中,她作为妖的恶的言行被削减删除,同时,为了“可爱化”白素贞的形象,又对她贤惠、仁义的一面进行了层层铺垫和渲染。例如,在讲述盗仙草的故事时,对白素贞形象则尤为用心回护,通过渲染相关正面情节,用以淡化“盗”的色彩,增加不得不“盗”的理由,并努力给“盗”增加有仁有义的内涵,增添有情有义的温度。这样一个白素贞,谁还会因为“盗”仙草救夫命而非难她呢。
再比如《四郎探母》中,有《盗令》一场戏。这里的“盗”,从剧情看,更非狭义的“盗”,只是借了“盗”的名而已。在金沙滩一战中,杨家将死伤惨重。杨四郎流落辽邦,化名木易,被招为驸马。宋、辽再起战端。听闻母亲佘太君押运粮草来至前线,杨四郎欲前往探望母亲。《盗令》之前的《坐宫》一场戏,已经交代清楚故事背景,铁镜公主也已经了解到四郎的真实身份。基于夫妻二人平日里的恩爱情谊,又加之相互信任,四郎还盟下重誓,才有了铁镜公主决意去母亲萧太后处盗取令箭,助四郎过关探亲。
对于《四郎探母》,著名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就其主要情节而论,这出戏精彩之处就是《坐宫》,《坐宫》的精彩主要是用优美唱腔来唱情;《盗令》(叫‘盗’就不合实际,应是‘骗令’或‘赚令’)之后戏逐渐散了,到了《回令》便成了顽笑戏。”在这段话里,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关于《盗令》的评价分析。他认为“盗令”应是“骗令”或“赚令”,这个说法确实特别准确。客观而言,之所以取“盗令”为名,应该只是一种笔法,为了从字面上提升一下戏剧悬念而已。仅就“盗令”的故事情节来说,并未因“盗”引发什么“槽点”,观众一直关注的其实都是杨家将的忠义、四郎和铁镜公主的恩爱以及佘太君与四郎的母子情深、重逢的喜悦、转眼又要分别的不舍之情了。
至于京剧《盗魂铃》,又是另一种情况。这是一出猪八戒盗取金铃的戏,名义上取自《西游记》,事实上《西游记》中也没这故事。这个戏版本很多,传承过程中改动很大。因为情节太闹腾,有的名家公开发言不演此剧。该剧还曾因被视为“闹剧”而被封禁。很多版本的演出,也根本没有“盗”什么事。比如,北京京剧院演出的一个版本,完全就可以当作一个古装小品看。循着基本剧情框架设置,演员相当放飞自我。京剧舞台上,刘、白、骆三派大鼓以及北京曲剧,一起上场;再加上男女反串,一人分饰三角儿,精彩热闹,别具一格。要不是演员“曲终奏雅”,临剧终提起盗铃,观众早都忘了这事了。
当然,在《盗御马》《三盗令》《三盗九龙杯》等戏中,主角们确确实实是盗得了“马”“令”“杯”;在《四进士》中,宋士杰确确实实是盗得了书信。在这些戏中,他们的“盗”,被称为“侠盗”。比如,《四进士》中,杨素贞以“为害夫霸产,谋卖鲸吞事”为由告状,素昧平生的宋士杰只是路见不平,凭着一腔扶弱济困的义气,决定出手相助。宋士杰偶然盗取住店差役所带的书信,并录在内衣上。这封信实在是太重要、太关键了。在这信中,巡按田伦向知州顾读行贿并因案件求情。宋士杰以此信为确凿证据,告状成功并终为杨素贞伸冤。宋士杰若无盗信之举,则根本无法得知、更无法取得田伦与顾读“密札求情”“贪赃枉法”“匿案准情”的证据,则这两位昏官必得不到应有惩处,杨素贞冤情也必得不到伸张。最终,这些“侠盗”留给人的印象,已是有“侠”无“盗”了。
戏里如此,从法律角度又该如何看待这些“侠盗”呢?在这方面,对墨家相关思想的解读,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另一种思考角度。《墨子》中有一句话说:“杀盗,非杀人也。”这句话直译很简单,意思就是杀盗贼并不是杀人,表达的是对贼盗的嫌恶。学界对于这句话的解释一直颇有争议。中央司法警官学院梁翠分析认为,从法律的角度审视,这一主张的提出源于“贼盗”对墨家“兼相爱,交相利”基本主张的严重背离和墨家强烈的社会正义感的驱使。这一观点与墨家“杀人者死,伤人者刑”的观点并行而不悖,也是墨家侠义观念的表征。如果用这个观点进行类比,我们可以推导出这样一个结论,人们对“盗”的反对与对“侠盗”的赞赏其实也可以是并行不悖的。当然,从法理上来说,其中还有诸多细节值得探讨,但“侠盗”蕴含的忠勇侠义思想和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价值观,无疑是非常宝贵的,是值得珍惜、弘扬的。
不得不说,这些与“盗”有关的戏,无论文戏还是武戏,都特别好看。看名家演绎这些戏,精彩之处更让人有酣畅淋漓之感。如《三盗令》,是一出脍炙人口的武戏。我在央视戏曲频道看过张云溪、景荣庆等艺术家主演的1983年版的《三盗令》。那时候,张云溪已经62岁。但他饰演的燕青,动作干净利落,表演似行云流水,把人物的英武潇洒刻画得淋漓尽致,看了真有一种荡气回肠之感。在《四进士》中,周信芳版宋士杰,表演“盗信”一场时,被高度赞赏“做工细腻”,评论界评价为“表演范例”。
戏里这样写“盗”,当然绝非鼓励盗行,或为盗开脱。对观众而言,都知道是说书唱戏,当不得真。看了这些“盗”戏,记住的反而是仁义、侠义。换句话说,戏中的“盗”也不过是个道具而已,要没有“盗”来推进故事,这戏就不太好演下去了。(大众日报客户端 于国鹏 报道)
责任编辑: 吕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