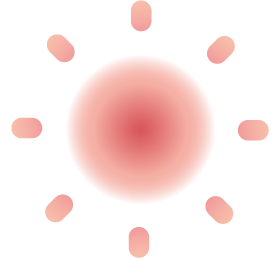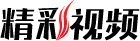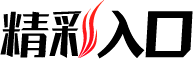文荟选读|陈光:比乡音更难改的,是母亲的“味道”
2022-05-07 09:04:04 发布来源:山东政协
母亲的味道
陈光

著名歌手林依轮2011年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妈妈的味道》,收录了林依轮与5位好友共同回忆妈妈亲手烹制的50道家常菜肴,包括蔬菜、海味、汤羹、甜品、主食和汤点,每一道菜肴都配以图文介绍,图片精美、菜式实用,让读者在浓浓的亲情氛围中,轻松学会烹制地道可口的家常菜,享受美味生活的乐趣,令人在翻阅的同时禁不住想动手一试。
读了林依轮的书,最大的感受是羡慕。羡慕林依轮有个富裕幸福的家庭,有个心灵手巧的母亲,让他从小就吃到了那么好的东西,学到了那么多的烹调手艺。羡慕之余,是深深的回忆,我想起了自己母亲的味道。
母亲的味道必然与时代相伴。我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是物质最匮乏的年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母亲的味道,自然是“清苦”。

记忆中,最早的母亲的味道是“窝头+咸菜”。家里有一个用土坯垒成的大锅台,上面支了一口生铁锅。锅里添上水,上面放一个笼屉。母亲把地瓜面、玉米面、高粱面用水和成面团,做成一个个类似捣蒜用的“蒜臼子”形状的窝头,摆在笼屉里。中间放一个大碗,里面是“辣疙瘩”咸菜条、葱花、姜片和几只干辣椒,再滴上几滴豆油。扣上锅盖,便开始烧火。母亲一只手拉着风箱,一只手往灶膛里添柴草。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隐约闻到香味,便是熟了。再等一会儿,母亲很庄严地揭开锅盖,雾气伴着香味立刻弥漫整个房间。那时候,每天能吃到窝头和咸菜,就觉得非常满足了。我从记事起,没有吃过比这更好的东西。
到了六十年代初,生活更加困难。母亲起早贪黑,弄来地瓜叶、榆树叶和各种野菜,掺到杂粮面里做成窝头,得用手捧着吃,否则容易散。再往后,粮食越来越少,母亲便把野菜剁碎,拌上少量面粉,放在锅里蒸熟,每人一碗,用手抓着吃。至于咸菜条,倒是一直有,这是母亲一生的保留菜肴。

这期间,母亲还经常用野菜做一种“小豆腐”。家乡有种野菜叫“青青菜”,叶子边上长满细细的白刺,很是扎手,摘下来放嘴里嚼碎,敷在伤口上可以止血。母亲下地拔来,洗净后先用开水焯一下,再用清水淘几遍,剁成碎末,趁着湿润,撒上一点豆面,用手慢慢拌匀。锅里放少量水,烧开后,把沾着豆面的野菜顺着锅边慢慢放入水中,用小火慢煮,不能沸腾,煮沸了豆花就飞了。煮熟后,点点白色豆末就粘在青青的菜叶上。母亲在锅的中间挖一个坑,让菜里的汤汁流到锅底,然后用勺子把汤舀出来,这样,锅里的菜就比较干稠了。这“小豆腐”软软的、滑滑的,闻着清香,吃着口感很好,连吃几碗,既可以充饥,又能够治疗由于饥饿造成的身体浮肿。多少年过去,母亲现在还经常做这种“小豆腐”,只不过“青青菜”少见了,改用小白菜、小油菜,口感反而不如从前。
细细想来,10岁之前,我就是吃着母亲亲手做的窝头、咸菜、小豆腐长大的。后来,生活一天天好起来,母亲的烹饪手艺便得到极大的展示。母亲做的饭菜,最大的特点是用材随便、工艺简单,成本很低,但味道极好。

不用多想,母亲最拿手的是做“菜饼”和包“包子”。
菜饼是用面粉和韭菜做的。母亲先把摘净洗好的韭菜切成末,放一点儿虾皮和咸盐,倒上花生油,拌匀待用。面粉用凉水和成面团,醒二十分钟,做成一个个大小均衡的面剂子。再把面剂子擀成圆圆的单饼,挖一勺韭菜馅摊在饼的上半部,把下半部对折上来,将边对齐,用拇指按压使之粘合得严丝合缝,不透风撒气。这样,一个半圆形的韭菜饼就做成了,接下来就是用鏊子烙制。烙饼的鏊子是生铁铸的,有三只脚,用砖头支起来,后面高,前面矮,底下烧柴草,烟火自然就会往后爬。烙饼是技术活,鏊子烧的不能太热,太热了面饼容易糊;但也不能不热,凉了容易把面饼烙干但还不熟,得掌握火候。翻饼要用木片做的长长的“刮子”,第一翻越早越好,然后就是翻来覆去两面轮着烙制。看到表面微微发黄起泡,再把菜饼用手招着立起来,专门烤一下饼的“背”,以免这里不熟。很快,外面的面饼熟了,里面的韭菜也基本熟了。韭菜不能太熟,太熟就烂成泥了,不好吃。待到全部烙完,母亲会用刀把一个个菜饼从中间一切两半,盛到铺着笼布的篮子里,放到饭桌上。面饼夹着绿色的韭菜,冒着热气,韭菜香,虾皮鲜,既好吃,又好看,令人垂涎欲滴。

母亲也经常用野菜做菜饼。院子里年年生长一种野菜,家乡叫“云青菜”,长得又高又大,母亲把叶子摘下来,先用开水焯、清水淘,再用做韭菜饼同样的工艺做成“挞饼”,相比韭菜饼,软软的,有点黏糊,同样好吃。“云青菜”一年生长六七个月,母亲的“挞饼”至少要连续做半年。
母亲做包子,多是用白菜做馅。工艺其实一点儿也不复杂:先选一颗大白菜,把外边的老帮子扒下来,切成丁,放点盐腌一会儿,用两只手使劲攥,把菜里的水挤出来。再切一点肥猪肉丁,放上葱姜末、五香面、酱油、花生油,用筷子搅拌,最后把白菜放入,荤素合成,搅拌成馅。包子皮要用发面,每个包子都要个大、皮薄、馅多。包好后先放在锅里醒一会儿,然后用大火蒸15分钟。出锅,稍凉,装盘,上桌,咬一口,白菜发脆,肉丁喷香,满嘴流油,真是过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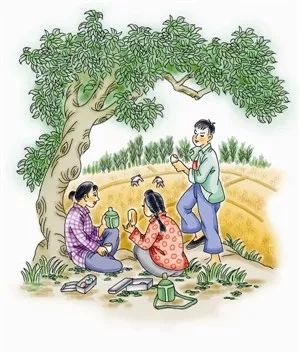
母亲做包子,也经常用萝卜缨子做馅。家乡把青萝卜、白萝卜的叶子叫缨子,每到秋天,萝卜收获,上面的缨子不值钱。母亲便买回来,择干洗净,先用沸水焯,再用清水泡,要换几次水,泡两三天,除掉青涩味,然后拧干剁碎,用做白菜大包同样的工艺做成大包子,照样好吃。剩下的萝卜缨子用开水处理后,挂起来晒干,冬天用水发开,依然做大包子,比起新鲜的萝卜缨子来,倒是另有一番风味。有时候,母亲也会先把萝卜缨子做成“小豆腐”,再把“小豆腐”放上葱姜油盐炒一炒,做一锅“小豆腐馅”的大包子,尽管里面没有肉丁,但同样好吃。
除了菜饼和包子,凉面条也是母亲的拿手好饭。“冬至饺子夏至面”,每年入夏之后,母亲就经常做凉面给全家吃。面是手擀面,卤子就两样:一样是豆角炒鸡蛋,一样是西红柿鸡蛋汤,提前做好凉透。面条煮好,用刚从井里打上来的凉水浸泡,然后捞出来放到大盆里,把炒豆角和西红柿汤一齐倒入,再放上捣好的蒜泥和多多的醋,还有切碎的香椿咸菜末。一人一大碗,有面也有菜,有汤也有饭,又凉、又香、又辣、又酸、又咸,吃一筷子面条,喝一口酸辣汤,打心里凉到肚皮外,从头顶爽到脚后跟,吃了一碗还想再吃一碗,吃了一次还想吃第二次。时间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母亲的凉面始终用料不变,口味不变。

记忆中母亲很少出远门,从没下过饭店,更没有拜师学艺,但母亲的炒菜技术却是一流的,可以说是无师自通。最让人称赞的是,母亲能把普普通通的大路蔬菜,通过粗菜细作,制出精美的味道,而且经常更换,让全家人饱尝口福。
母亲做得最多的是清炒萝卜条。那时候没有反季节蔬菜,普通老百姓家全年下来基本就是“萝卜土豆白菜”。母亲先把青萝卜切成细条,用清水浸泡,去除萝卜的辛辣味。再拿一丁点五花肉切成末,干红辣椒切成丝。热锅放花生油,葱姜末爆锅,辣椒丝和肉末放入,加酱油炒熟,然后放入萝卜条,迅速翻炒后加入醋和盐,再翻炒后出锅。这道清炒萝卜条,因为比较早地放了醋,吃在口中,萝卜非常清脆,微微发酸,香中带辣,比别人家的水煮萝卜片儿不知好吃多少倍。母亲还会同时烙上一筐单饼,一张单饼卷上一筷子萝卜条,外软里脆,两只手攥着大口吃,简直是美极了!用同样工艺,母亲还经常做醋溜土豆丝、清炒白菜芯等菜,放上点泡发好的地瓜粉条和香菜梗,就更好吃了。

酱爆扁豆也是母亲经常做的菜。每年春天,母亲都会在门前屋后和墙边种几棵扁豆和丝瓜,很快就果实累累。尤其是扁豆,秋风一凉,就可着劲地长,一朵朵蓝色的小花非常漂亮,一串串的扁豆挂在蔓上,隔几天就摘一小筐。母亲先把扁豆两边的筋摘除,然后洗净切成宽宽的条。葱姜蒜末爆锅后,放入母亲自己发酵制作的甜面酱、酱油和少量水,慢火熬制。待酱汁渐浓时放入扁豆翻炒,一直炒熟,最后放盐。吃的时候,咬一口馒头,夹几片扁豆,慢慢咀嚼,细细品味,香中带甜,很是可口。吃完了,还要用馒头擦干碗里的酱汁儿。用这种工艺,母亲还经常做酱爆茄子、酱爆辣椒,偶尔还做一次酱爆小河蟹,每次都被吃得干干净净,一点不剩。
比起这几样青菜,母亲偶尔做一次“辣子炒鸡”,那可真是令人欢呼了。小时候家里穷,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一般是家里有什么喜事的时候,母亲就赶集买回一只小公鸡,杀了后剁成花生米那样的小块。先炒鸡肉,要放上八角、大料、葱断、姜片、酱油用水煮,基本煮熟后,再把一大盆切碎的辣椒放进去,鸡肉和辣椒的比例至少是一比十。待到汤汁收缩得差不多了,菜也就成了。上桌后,我两眼紧盯着菜盘,筷子直接朝着那里面的鸡块伸,尽管肉很小,但很珍贵,放到嘴里,细细地嚼,连骨头一起咽下去。当然,辣椒也会一齐吃掉,最后连汤也不剩一点儿。母亲舍不得吃,只是静静地看着我们。当时我就想,如果将来我有钱了,一定请全家吃炒鸡,鸡肉要切得像核桃那么大,尽着吃,吃个够!

记忆最深的还是母亲做的“酥鱼”,那可真叫一绝。上世纪七十年代,很长一段时间,我家住在寿光北部的小清河边。到了秋天,坑坑洼洼凡是有水有草的地方,一定有鱼,大多是鲫鱼,也有鲤鱼和鲢鱼,都是当年生,最大的像巴掌。每到星期天,我和弟弟扛着网子,抬着水桶,四处捞鱼。半天下来,满满一桶,总有十多斤。母亲把鱼的内脏摘除,开始做酥鱼。那时候家里食油很少,只能用这种方法。母亲先在锅底铺上厚厚的白菜叶,然后把鱼一层一层整整齐齐地摆上,等到全部摆完了,再在上面盖上白菜叶,把鱼压住。再加入食盐、酱油、醋和水。醋一定要放足,酥一锅鱼最少要放半斤醋,水要没过鱼和上面覆盖的菜叶。接下来就是烧火,大火烧开,煮5分钟,撇去浮沫,转入文火,看到锅面上冒泡儿即可,不能翻大滚。连续两个小时,等到汤熬尽了,最底下的白菜微微糊了,这酥鱼就做成了。母亲先用筷子把上面的白菜揭开,然后用铲子把鱼一条一条盛到盘子里。做好的鱼微微发红,看似非常完整,实际上连骨头都酥了。吃起来香香的、咸咸的、酸酸的,连骨带刺一起吃,鱼头也不剩,一点儿也不浪费。那垫底的白菜也别有一番风味。因为鱼是自己捕的,酱油和醋价钱也不贵,这道菜成本很低,全家可以放开吃,每到这时,就是全家最开心的时候。

时代在变,母亲的味道也在变,但一直不变的是母亲做的“咸菜”。咸菜是普通人家的当家菜。每到秋天,母亲早早把大缸准备好。等到大田里的“辣疙瘩”收获,母亲一次就买两百斤。用镰刀削去上面的根和毛,清洗干净,放入大缸。放三层疙瘩,撒一层盐粒。最上面摆上木板,压上石块,灌满清水。要确保水漫过木板,防止疙瘩漂上来。三个月后,咸菜腌透,就可以吃了。这一大缸咸菜,足够全家吃一年。母亲把疙瘩咸菜切成丝,或者切上葱丝加点香醋生拌,或者用猪油炒熟,总之每顿饭都上一盘,很是下饭。七十年代初,我和弟弟在镇上上中学,离家15公里。每到周末,母亲把炒好的咸菜装满一小罐,让我们提到学校,这就是兄弟两人一周的菜了。为了保证营养,母亲特地在咸菜里放了炼制猪大油时剩下的油渣,特别香。上学几年,我和弟弟吃了几十罐咸菜,那味道至今不忘。
18岁之前,我基本上是天天吃着母亲做的饭菜长大的。18岁以后离家创业,母亲的饭就渐渐吃得少了。开始每周一次回家,以后每月一次,再往后越走越远,就几个月一次了。时光如水,转眼间40多年过去。时代变了,国家变了,社会风气变了,人的生活习惯变了,但母亲的味道始终没有变。每次回家看望母亲,仍然是小时候吃的饭。春天回家,一盘大包子,热气腾腾;夏天回家,一盆凉面条,清爽可口;秋天回家,一碟酱爆扁豆,一碗丝瓜炒鸡蛋,两个馒头;冬天回家,一碟清炒萝卜辣椒,一碗白菜炖粉条,两张单饼。至于疙瘩咸菜条,那是一年四季必备。吃着母亲做的饭,除了可口,还是可口;除了舒服,还是舒服。

世人都说乡音难改,我说母亲的味道难忘。母亲出身贫寒,一生没有享过福。是她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含辛茹苦,拉扯我们兄妹几人长大。如果说林依轮的妈妈的味道是山珍海味、美味佳肴,我的母亲的味道就是粗茶淡饭、清粥小菜;就是勤劳善良、勇敢坚强;就是勤俭持家、艰苦朴素;就是无怨无悔、真情大爱。母亲的味道伴我一生,教育我老老实实做人,鼓励我扎扎实实做事,引导我一路前行、不跌跟头。
走遍万水千山,走不出母亲关怀的视线;尝尽了生活百味,才知道母亲欣慰的笑容最甜。又是一个中秋月圆,我携孙儿回老家看望母亲。又一次吃到了母亲亲手做的饭菜,还是那熟悉的味道。看着母亲一丝一丝的白发、一条一条逐日渐深的皱纹,我的心里不禁慨叹,这就是多年含辛茹苦哺育我成人的母亲啊!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最伟大的母亲!儿子永远不忘你的恩情,愿你好人终有好报,永远健康长寿!

临走时,弟弟把母亲亲手炒的一盒咸菜递到我的手上,并打开盖子让我闻闻,还是那细细的疙瘩条,点点的油渣,红红的辣椒,从小就吃但永远也吃不够的味道。
回程的车上,我打开收音机,找到了歌手刘桐的那首歌《妈妈的味道》。“尝尽天下佳肴/总不如妈妈的味道/享尽富贵荣华/总难忘妈妈的歌谣/你的青春/写满了操劳/你那勤劳的双手/编织着家的美好/历尽人间冷暖/更眷恋妈妈的怀抱/看尽世态炎凉/更想念妈妈的唠叨/妈妈呀妈妈我爱你/孩儿的一切都是您的骄傲/妈妈呀妈妈我爱你/让孩儿为您抹去岁月苍老。”女歌手的声音感情满满,听着听着,我的泪水湿了眼角。

我记起了印度一位先哲的真言:“世界上一切其他都是假的,空的,唯有母亲才是真的,永恒的,不灭的。”还有高尔基的话:“世界上的一切光荣和骄傲,都来自母亲。”他们说得真对,说得真好!
2019年9月17日于泉城
责任编辑: 禹亚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