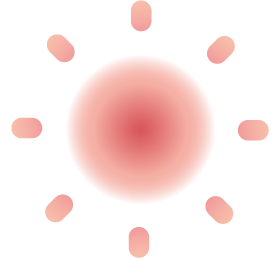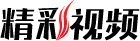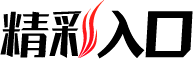日记寻珍|顾颉刚与山东的缘分
大众日报记者 卢昱
2023-05-25 15:46:10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130年前,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在苏州出生。100年前,顾颉刚30岁时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集中表达了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此后,顾先生的历史学研究以由其引领的“古史辨”运动及七大卷《古史辨》为代表,直接促成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结构性转向,奠定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基础。
同时,顾先生兴趣广泛,一生保持着旺盛的好奇心,在民俗学、上古神话学、故事学、宗教学、民族学、边疆地理学等领域,亦皆可谓开风气之先。
顾颉刚与山东的缘分很深。他出生时,父亲顾子虬正在山东武定府知府潘子牧家教读,一年工资加到70千文,他懂得生活的艰难,除了剃头之外,一钱不用,都寄回家;同时用功读书,以期上进。那时祖父为顾颉刚算命,命里缺土、缺金,加上排行是“诵”字,因此起名“诵坤”,字曰“铭坚”。稍长后,顾子虬取名字相反的古义,又起了一个号叫“颉刚”。
1927年夏,胡适曾评论说:“我与傅斯年的性格是向外发展的,顾颉刚的性格是向内发展的。”此话说得不错,顾颉刚头脑里永远装着许多问题,不停不歇地思考学问、工作和生活,剖析他人和自己。在顾先生“其心也诚,其志也坚”的治学历程中,与齐鲁大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以1931年在山东的游历最为密切。

这种向内发展背后是大学者忧民忧国的情怀,在顾颉刚游山东的日记中足可见。1931年,顾颉刚与同事组成燕京大学考古旅行团。“旅行目标,一方面为校中图书馆及小型博物馆搜购文物;另一方面则以连年天灾人祸,历史文化之遗存必受摧残,将调查其损失及现状。”所到之处有:河北之定县、石家庄、正定、邯郸、魏县、大名,河南之安阳、洛阳、陕州、开封、巩县,陕西之潼关、西安,山东之济宁、曲阜、泰安、济南、龙山、临淄、益都、青岛等。
在山东,顾颉刚看了曲阜三孔,到泰安游岱庙及蒿里山;在济南看了趵突泉,“泉在市场中,适新遭火灾,触目皆枯椽焦柱。泉有三潭,向上喷吐,势极猛,周约三尺,此他处所未睹者也”;之后,他到山东省图书馆,见到馆长王献唐,并由其陪同参观。看完馆藏的汉画石、鼎彝、书画及善本书之后,顾颉刚评价说:“以王馆长之勇猛精进,数年以后必将蔚然为北方文化重镇矣。”
顾颉刚一行还游龙洞、千佛山。在千佛山,顾颉刚看到民生之艰,“以离城近,进香者多,故寺院甚新,路亦平坦。丐又多于泰山,每登数级,即遇其一。”在看到不多的几处佛像和石刻后,顾颉刚有些失望:“久闻千佛山名,以为佛像必多,搜之竟不再见。叩之寺中人,亦无以答。”之后,顾颉刚还到城子崖访谭国故城,去捡拾“石陶器”等文物,居然能“得石斧一,黑陶碎片若干”。接着又踏访了平陵故城。
可惜在济南时,顾颉刚未能与老友王祝晨相见。早在1926年,王祝晨被军阀张宗昌撤职后便想把“山东民俗集成”整理成册。王祝晨在二中、一师担任校长时,鼓励学生寒暑假回乡收集山东各地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风俗礼仪、民谣、民谚、民间游戏方法与游戏玩具等等,他以每日十小时到十二小时的工作量来整理、手抄出六大门类,并与顾颉刚书信来往研究出版之事。
此后,顾颉刚一行出临淄故城东门,游黔敖墓。下午到青州,观文庙,又到衡王府,看石牌楼、胭脂井、四松园等遗迹。上南门,望云门山,循城墙,步至东门,游文昌宫,观大齐碑。由城外至北门,看东阳故城。进北门,游万年桥、玄武庙,看龙兴寺钟。还到范公亭,看井亭及明清诗石刻,游城隍庙。
5月18日晚,顾颉刚到达青岛,此后他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会友、访古。5月21日晚七点半,顾颉刚在青大演讲《黄河流域访古之经过》,向青大的学子介绍他一个多月来在黄河流域访古考察的经历,历时一小时二十分钟。从顾颉刚的日记记录来看,他行程东西几千里,演讲的内容就近取材,在旅行中的见闻随手拈来,跨越上下五千年,以期激发学生对历史地理、考古访古的学术兴趣。可能在座的青大学子对考古、文物并不是很感兴趣。这对顾颉刚来说,则有些怅然若失,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究竟不是一个能演讲的人,今日费时虽多,但听众无甚兴味。先走者甚多。我想,即以此为我演讲的末次吧。”
顾颉刚一路考察,所见先民之遗产,“或建筑之伟,或雕刻之细,或日用器皿之制造,或文字图画之记录”,莫不惊心动魄,但“何意此二三十年中竟受急剧之破坏,及我之身将沦胥以铺”。这次旅行,所见的古迹古物残毁的情状,固然大可伤心,但真正使顾颉刚最伤心的倒不是这些,而是国计民生的愁惨暗淡实况。

不难看出,此行之后,对顾颉刚思想的冲击,足以影响一生。作为一个“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学者,顾颉刚久居都市,已习惯了现代化生活,对于现实的民间本来是孤陋寡闻的。此行使之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新的认识。
5月29日,顾颉刚回到北京,仔细回味旅程,彻夜未眠。尤其是,他所见民生惨痛状况,感受到强烈的刺激:“他们许多人还度着穴居的生活。自虎牢以西,土质甚粘,山又无石,所以容易开洞……我们为了休息,进过多少乡村人家,我用了历史的眼光来观察,知道炕是辽金传来的风俗,棉布衣服的原料是五代时传进中国的棉花,可称为最新的东西。其他如切菜刀,油锅之用铁,门联之用纸,都是西历纪元前后的东西,可以说是次新的……然而他们所受的压迫和病痛却是二十世纪的,官吏和军队要怎样就怎样,鸦片、白面、梅毒又这等流行,他们除了死路之外再有什么路走!”
对于“亡国”之说,因当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成国民常识,顾颉刚自然早有此种恐惧;然而对于“灭种”,生活在城市的顾颉刚以前没有这种感觉,但在这次亲历华北农村之后就清楚地体悟到了。几天后,他回到学校里,看着大家无忧无虑的容颜,不禁对朋友说:“你们不要高兴了,中国人快要灭种了!”人家听了,只觉得他言之过重。即使相信了他的话,也只有作同情的一叹。从此以后,顾颉刚觉得在研究学问之外,应当做些事了。
就是这一年的秋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沦陷。别人悲愤填膺,顾颉刚则认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起死回生的机会。“我以为如果没有这件事,我们的国家是亡定了,我们的民族是灭定了,再也翻不起来了。现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气,毕竟还有起死回生的一点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没有等我们绝气就来抢我们的产业,激起我们的自觉心和奋斗力,使得我们这一点希望能够化成事实,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我们应该捉住。如能捉住这个机会,帝国主义便真可打倒,中华民族便可恢复健康了。”作为学者,顾颉刚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以为当时最要紧的任务,是抓住这个机会唤醒民众。
华北之行,也让他人生的自我选择彻底定型。他幼年读贤书,颇有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但到年纪稍长之后,深知世界情形的复杂和一己知识的短浅,觉得自己这一生只配研究学问,而毫无“用世”之心。此行之后,即便对社会诸方面感到不满意,他总以为自有贤者能者担当责任,不必以自己不适合的才能投入其中,弄得于世无益,于己有害。所以十余年来,虽然国事“如沸如羹”,他始终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卢昱报道)
责任编辑: 杜文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