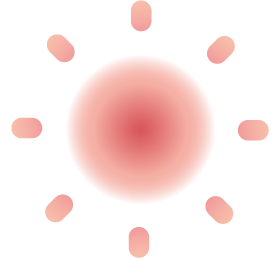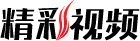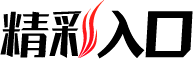【乡趣乡愁】我的叔叔
2022-05-27 10:33:39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 闻思哲
时常会想起我早已过世的叔叔,总是心心念念在想他,想起来的时候是那种心会一疼的感觉。
总觉得我与叔叔情未了。他的许多事情会不经意地在我脑海中呈现,想写写我的叔叔的念头也时时地涌起,甚至有时候觉得不写就对不起他,或者说总觉得有很多对不起叔叔的地方,让我想通过写他来平衡下我的心理。
有那么几次走在济南的街头,还有几次是不经意地从车窗里望出去,看到一个瘦高个子的老男人站在路边,从脸上几乎看不出表情,穿着极其普通,就像是一个收破烂的,或者打什么其他零工的人,也许要过马路,或者像在等什么人,东张西望的,乍一看,竟然有点像我叔叔的模样。我就忍不住多看了几眼,想象着是叔叔站在那里。

有段时间,我知道了量子纠缠。从网上也看到世界上长得相似的人的照片比对,从照片上看相似度非常高,有的几乎就是双胞胎,而且出身、经历、职业、爱好,甚至服饰,甚至伴侣,也有很大的相似性。可实际上他们一点血缘关系也没有。我就在想,是否真有另外一个“我”、另外一个叔叔,在平行空间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也许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是双生的,一个在这里,一个不知道在哪里。如果真是这样的类似孪生的纠缠,我也不知道我用的纠缠这个词是否准确,那么这种纠缠就非常值得研究了。
我的父亲是兄弟两个,还有两个姐姐。姐姐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是同父同母的,只不过,我的爷爷奶奶去世得早,父亲后来过继给二老爷爷(父亲说这叫隔儿过孙),很快也成了孤儿。叔叔则过继给寒修爷爷,我的那个奶奶叫聂玉美。在我小时候的概念中,叔叔家的日子虽然也不富裕,但是总体上比我家要强很多。按照我父母的讲法,他从小没有吃多少苦。
记忆中有关叔叔的似乎是比较晚的。我现在往前想,大概是我刚上学,应当六七岁吧,上小学一年级。那时候农村兴扫盲,我的帮扶对象是我婶子。我这人认真,天天去教婶子识字。一放学我就缠着婶子,非要检查她记住了哪几个字,还要逼她再学几个新字。有一次婶子的娘家兄弟来了,一个很和善,说话就带笑的农村赤脚医生。婶子正在跟人家说话,一见我来了,婶子说,文子,你舅来了,我们俩说说话,今天不学了。我根本是不管不顾,仍然坚持让婶子学。婶子无奈地看着我,我这个舅也笑哈哈地看着我,说,学吧,学吧,这孩子真好。

那时候那个老宅子还在,正房三间北屋很有气派,正中是一个月台,月台的西面有一棵石榴树、一盘碾。有时候我一边帮婶子推磨,一边教她识字。
有一天早上,小孩子也是百无禁忌,我也忘记了。那时候叔叔也不大啊,叔叔家的弟弟昆迎和妹妹瑞华已经有了吧。我一大早还想着去教婶子,就急匆匆地跑进了叔叔和婶子的房间,那是在北屋的东间,一盘大炕上,叔叔睡在西半部,婶子睡在东半部,弟弟妹妹靠着婶子东侧睡,一大家子人盖着一床被子。我天不怕地不怕,当然也是不懂,一进来就拽着被子往上掀,结果吓得他俩抓紧掖,结果还是被我看到了他们似乎啥也没有穿。当然,那时候咱心里还是纯洁的白纸,啥也不知道,啥也不懂。
想起来这个画面,我还想起来叔叔算作个读书人,因为炕沿放着的几本书,似乎有三国演义,也有水浒传。只不过,我印象中那些书好像也不完整,好像散了页一样。现在那些书肯定也找不到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向叔叔要来看。
叔叔的识文断字我也是见识过的。那一年,1994年,我与彭女士结婚,在我妹妹的饭店里摆酒席。叔叔对此是非常重视的,我记得那天他好像穿得比较正式,是西装还是中山装我忘记了。更加重要的是,他老人家拿出了一张纸,是他老人家做了一晚上功课,写了一篇祝酒词。他就那么极其庄重地、极其郑重其事地念着。虽然也是讲欢迎感谢亲朋好友,讲结婚如何重要,如何早生贵子,如何相敬如宾,如何持家之类,还有美好祝愿之类吧,具体是啥内容我也记不得了,但是只记得叔叔写得跟那些我们通常听到的不太一样,半文半白,一听就知道是早年读过书的才写得出来。那天是我姑姑家星子哥在录像,哪天我再找找看,看到底穿的啥、讲的啥,反正是比较正式吧。或者这是不是叔叔唯一的影像资料?谁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呢?

写着写着,小时候在农村的那些事情就一一浮现出来,比如各种各样的吵架。
那时候吵架在农村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我们这些小孩子,包括大人们,听到哪里有吵架的声音,立即就闻声而动、循声而去,不光小孩子,也有大人。大家围在一起,不像是看打架,完全是看热闹,劝的也有,不多,更主要的是围在一起议论,指指点点,说着谁的不是。说看打架,有时候就像看演戏,看谁的声音高,看谁的拳头大,看谁吃亏,看谁赚公道。这种现象叫啥呢,也许是那时候农村的娱乐方式比较单一才有的吧。
我印象中跟叔叔有关系的吵架有三种。之所以用种,是因为有些吵架是经常进行的。第一种是叔叔、婶子跟我父母的。起因是老辈子传下来的一张小小的三抽桌,我老家叫抽头,好像是榆木的,长方形的桌面,下面三个方形抽屉,再往下一个稍大些的两扇门橱子,四根腿子撑在地上。我家可能就这么一个老物件,可能叔叔婶子觉得涯庄我舅老爷主持分家时不公,多给我家这么个东西似的,所以想起来就吵着要讨回去。当然,肯定是要不回去的。每次吵过架不多时,叔叔很快再来我们家,跟我父亲又喝茶又聊天又抽烟的,我父亲那时候好像也抽烟。两个人似乎都说没啥大事,把责任往女人们身上一推了事。过一段时间不知道因为啥事又吵起来了,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就又翻腾出来,还少不了这张抽头。这也是人穷逼的吧,针眼大的东西都看得比斗大。需要说明的是,这张抽头现在也不知道哪里去了。

第二种是我跟叔叔吵。比如马上就要除夕了,父母让我去叔叔家借个大盆,借个水桶,好像还有秤。我想叔叔婶子对我一向很好,肯定是手到擒来。我兴冲冲地跑到叔叔家,其时叔叔正在大锅头上做豆腐,手里拿着浆布袋,一提一压,穿着短衣服还一头的汗,整个小东屋全被热气弥漫着。我进去诉说我的使命,正想拿着东西走,叔叔大喊一声,你没看正忙着吗,这些东西还得用,你回去吧。我一听就烦了,破口大骂,而且是叫着叔叔的小名来骂,边骂边蹿出门去,说再也不来了,你也不用借俺家的东西,一路哭一路骂到家。当时只知道生气了,后来这件事情怎么平息的记不得了。肯定有一节是我娘找我叔叔,肯定也是没好气地骂一顿,肯定数落得叔叔不轻。现在想来,还是小孩子不懂事。实际上,我也不止一次跟叔叔吵过架,骂过叔叔,这都是小时候的事情。
叔叔还种过瓜,就在村北头,种的是甜瓜。那时候知道叔叔在管着,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孩子的心思。我是经常去那瓜地看啊,就盼着甜瓜赶紧长出来。眼见的瓜蔓(老家念万)子长出来了、密了,眼见着开花了、坐瓜了,眼见着瓜大了、瓜香味出来了,绿的是蛤蟆(老家念hama)翠,脆中带甜;黄是老面瓜,面中带甘;黄绿相间的是芝麻香,香似芝麻。我本是个馋猫级的人物,天天围着瓜地转来转去,只是叔叔在地里也舍不得摘个给我吃,我心里那个恼火啊,有这样的叔叔吗。直到有一天晚上,叔叔来我家,拿着个篮子,篮子里有几个瓜。叔叔给我父母说,给孩子们尝尝吧。边说边对我说,你这个皮孩子,以后尽量少到那里去,去了我也不给你瓜吃,那是队里的瓜地,一是我说了也不算,二是我管着,给你吃,那算啥呢,人家那么多人看着呢。可是小孩子的心里是不多想的,就以为叔叔对自己不亲,太小气。

到了我上初中的时候,1980年左右吧,我上初一。又是马上过年了,叔叔有天晚上来到我家,拿来一件新衣服,是一件黄上衣,好像是涤卡布的。叔叔说,我们队里今年结算工分,家里分了40来块钱,我给文子花5块钱买了件衣服,算是对他学习好的奖励吧。年年得考第一啊,给咱老徐家争光。这件事情使我转变了对叔叔小气的看法。全年的收入就是40块钱,拿出5块钱来,这得下多大决心啊。按照这个比例,我得回馈叔叔多少呢?这个账真不能算,也不敢算。就这个事,我一直不忘,想起来就愧疚。后来这件褂子我穿到了周村一中,那是1983年了,其时我们几十号人住在一中院内西北角邻近马路的一大间集体宿舍内,我是后来的,加了张床,床就放在整个屋子的中间。有一天,我的黄褂子后背中间部位不知道被谁用刀子从上到下割了一道,得有20多厘米长。这一刀割得我好心疼,那时候这也属于贵重物品。为此我大骂了一通,也没有人接茬,只好罢了。
第三种吵架是叔叔跟婶子吵。叔叔脾气上来异常爆躁,脏话张口就来,而且还动手打婶子,两个人时不时地支起架子就打。打得严重了,有一次婶子喝了农药,口吐白沫,一家人吓得抓紧拉到公社的医院去救过来。这种打架婶子是打不过叔叔的。通常情况下,就跑到我家里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少不了我父母一顿说,各打五十大板。这类吵架,我父母之间也经常进行,有时候也比较惨烈,吓得我们几孩子哇哇地哭,不知所措。不过经常是我母亲占上风,我父亲1米8几的个子,母亲才1米5多一点,不知道战况为何是这样。是父亲让着母亲,还是其他原因不得而知。只是近年来,好像情况发生了变化,父亲有时候发脾气,母亲就打电话来告诉我:“我去济南跟着你过,你找车来拉我吧。”起始我还劝着,后来有位好朋友说,你就激下老人吧,告诉她你俩离婚吧。后来每逢到这种情况,我就说这话,老人果然也就没了下文。

叔叔也算脑子比较灵光的人。除了做豆腐,他似乎还在生产队里做过粉条,跟我父亲打过钢球,也像我父亲一样收过破烂。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走村串集,包括去张店周村做过鸡蛋卷来卖。下面是一个小炉子,上面坐着一个简单的工具,两片有纹路的厚铁板夹在一起,打开,舀一勺鸡蛋面糊均匀地摊开,一压,然后放在炉子上翻烤,差不多了,就打开铁板,把鸡蛋饼卷起来,放在篮子里待卖。面糊里面放了糖。面的香,加上糖的甜味,弥漫在空气中,很是招人,所以卖得挺好。那时候我叔叔家的大妹妹瑞华跟着她,打个下手,也帮着收个钱啥的。叔叔告诉我,得看紧点,别跑了幅子。意思是说,妹妹有时候算不好账,少收了钱,或者妹妹私下留着几个小钱。有很长一段时间,叔叔的生意很好,见到叔叔总看到他笑的样子。持续了一两年吧,突然有一次,我就问起叔叔,他说生意维持吧,看着挣钱,又有人家也做了,买卖一争,利就薄了。后来,我到济南上学。正是“康师傅”最时尚的时候,我的丝绸学校的同学梁绍德经常给我送给养。有一次就送我一盒“康师傅”蛋酥卷,吃起来入口即化,真是人间美味。我就想起来叔叔做的蛋酥卷,只不过厚点罢了,味道并不错。“康师傅”能够在中国扎下根,能够发展到今天,我们真得向人家学习,既有本土元素,又有所提高和改进,进而引导消费,做得确实不错。直到现在,我到集上看到有人做这样的蛋酥卷,或者拿到“康师傅”,总想起来叔叔,想起来他在集上的样子。

后来叔叔就病了,我老家叫吊线疯,其实就是脑血栓的后遗病症,嘴歪得不成样子,有时候还从嘴角流出来哈喇子。
对于叔叔的病我还是很用心的,千方百计找医生,西医的、中医的,正路的、偏方的。甚至我请我母亲去威海找一个著名的中医姜主任给诊治,后来还有济南的各大医院。我的母亲陪到威海,一直待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威海的人都说,嫂子比老婆还好,人家陪小叔子在这里待这么长时间。再到后来,山东省立医院的一个朋友说,恐怕很难治了,现在进入缺钾阶段,听了以后只觉得怎么会这样呢。
叔叔的状况真的一天不如一天了。
后来叔叔就回到了老家,而我每次回老家的时候一般都会去看望他。
看了几次呢,我想大概不超过两次。
第一次,我去看叔叔的时候,他搬到正房的小东屋了,当然也是改造了,窗明几净,只是你一踏进去,就感觉满屋的空荡荡。叔叔就坐在席地而搭的小床上。

他一看我来,就高兴了,尽管因为嘴的原因说得不太利索了,听上去呜呜噜噜的。
我心里难过,但也不敢让他看出来,还得忍住别流泪。一边看着他清瘦的样子,一边说,叔叔,你的病呢,主要靠你的信心,你得有信心。
我一转眼看到了墙上挂的二胡。我拿下来,交给他,然后说,叔叔,你还能拉出来吗,你试试。叔叔听我的话,真的操起了二胡,在他的操作下,二胡竟然咿咿呀呀地拉出了声,只是真的已经不成调了。
我说,叔叔,你得坚持拉,自己挑战下自己,争取恢复。叔叔看着我说,好,我听你的。
从叔叔家出来的时候,我已经预料到叔叔来日无多了,眼泪禁不住流下来。
后面的事情已经不需要再说了,没有过多久,传来了叔叔的死讯。
从济南回周村老家,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基本上是流着泪回去的。到了老家下了车子,泪还是忍不住。见了我娘,我就放开声哭起来,总觉得我没有尽到孝心,没有看好叔叔的病。直到今天,我还没有完全原谅自己,我觉得我尽得心是不够的。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衡量。

到叔叔家,按照老家的风俗,我被摆布穿上了孝衣,说是被摆布,只是因为我那时候只是止不住地哭,我无法控制我的情绪,又不敢大声,只是用心在哭着,更多的是一种掏心的低泣。
我掀开盖着黄表纸的叔叔的脸,嘴依然歪着,没有合上,眼睛我已经记不清了什么样子。他张着的嘴,是不是因为最后没有见到我呢,还是想最后给我说点什么呢?可他张着嘴,真的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今天,我是带着剖析我自己的心情来写这段文字的。
世界上最大的无助,莫过于你眼看着你至亲的人一点点走向生命的终点,而你却无能为力。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是一句古话,表达的是至理。时间总是有自己固定的步伐和节奏,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对于老人的尽孝,对于有恩于己的报恩,对于想做能做的好事,是不能有片刻耽搁的。老人不会等你有闲之时才去尽孝,恩人不会等你有闲之时才去报恩,好事也不会等你有空。所以,此念一起,就不要放下,就要抓紧化为行动。否则等待的结局也许就是一种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和心亏。
叔叔算个什么样的人呢,一个极普通的老百姓罢了。

他的一生为生计而奔忙,他的木讷而少语,他的倔强而爆发,他的向命运的抗争,他百般算计中的贫穷,他默默抽烟的样子,他难得的爽朗的笑,我似乎永远都没有忘记,似乎一想他,这些就会浮现在眼前,恍如昨天,恍如当下。我总觉得他每天在拖着沉重的心情前行,每天都在为生计而奔波。相比而言,我所谓的理想,所谓的崇高,所谓的神圣,实在离他太远太远。因而,我无法用高大上的语言来描述他,甚至他的行为仅仅就是一种存在,与高大上无关的存在。举个例子说,他跟我寒修爷爷、玉美奶奶关系都说不上好,甚至在我眼里,他们毕竟收养了他,可是他实在算不上孝顺;比如,他的家庭教育,甚至连过得去也实在算不上;再比如,他勤俭得近乎吝啬;甚至他与我父母、与我姑姑、与我们这些小辈们的关系处得还欠亲密,等等。这些实在也算不上优秀的品质或品行。
如果说叔叔有闪光点的话,在我的记忆中,他眼睛中闪着的亮光,尽管偶尔才出现,尽管更多的时候是无神的浑浊或者浑浊的无表情,尽管像昙花一现,还是表达了那种真诚和真实。这种亮光,出现在过他看我的眼神中,或者我想他一定遇到了开心或者得意事情的时候。我只能大胆猜度,在他的心灵深处,是这样一种生发逻辑:哪怕有一丁点的愉悦,也会冲破所有的包裹去进行一次灿烂地释放,这种释放,也许是他平衡现实世界、物质世界的唯一稻草。

怀念叔叔,是因为亲情,是因为愧疚,更是因为我心里永远有着的真实的存在。叔叔不是狡猾的、虚伪的,因为他来不及、顾不上,没有学会、也没有必要伪装。就此而言,叔叔是活着的,以他自己的方式。就此而言,叔叔活得是轻松的,以人应有的尊严。还有什么比真实更珍贵,更值得纪念呢。
黄表纸下叔叔的眼睛是什么样子,我真的记不清楚了,但他生前与我对视时闪射出的亮光,我依然记得。
对了,我的叔叔是德字辈,名盛,有时候也写作胜,是一个很好的名字,1944年8月初5生的,2010年8月初3下午4点没的,去世接近12年了。
责任编辑: 刘君 签审: 于国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