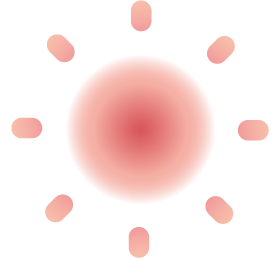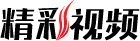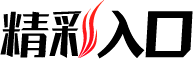“我与父亲”征文‖儿时三跪
2021-06-19 11:39:22 发布来源: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

不管是养育型父亲、学习型父亲、传统型父亲还是现代型父亲,去掉这若干定语,“父亲”永远是个刚柔并济的词汇,他在平淡中给我们最永恒的安全感。
难忘很久以前看过的一个很美的画面:是“母亲”辛苦地找来小虫、草籽、露水,喂给嗷嗷待哺的小鸟,是“父亲”奋力把这温暖的巢穴筑在向阳的坡上。
还记得早年课本上朱自清的《背影》描述出那份深沉的父爱,这一份父爱犹如月光平凡而美好、无声而温馨。
不同的人,对父爱的感受和体会自然不同。
父亲节来临之际,大众日报客户端联合大众日报丰收副刊推出“我与父亲”主题征文,聊聊你和父亲的故事,文体不限,内容可以是回忆往事,也可以是你的节日创意,还可以是你节日当天的亲身经历。
投稿邮箱:fengshouliujun@126.com

儿时三跪
□ 廖红继
父亲是转业军人,在县城工作,周六下午骑自行车回来,是上海永久牌的,威严得很。父亲属牛,平时沉默少言,一脸严肃。我的表哥准时来到我家,学骑自行车,一大帮小孩围跟在后面,村子里清脆的铃铛声响个不停。家里厨房飘香,母亲烧得一手好菜,父亲和大舅爷、姑父、伯父们喝着小酒,高声谈笑,一个个满脸红光。我和弟弟妹妹围在热气腾腾的灶台边,看着母亲煮的一锅荷包蛋,馋得不停地要,母亲哄着说:“先给大人们盛上,一碗四个,他们会客套留一个给你们的。”于是我们躲在门后面,从门缝里看他们吃,当数到第四个的时候,弟弟妹妹们哭着说:“一个都没留,”听见哭闹声,一向严厉的父亲居然乐呵呵看向我们,大人们连忙放下碗,一脸愧疚,我们满足地吃完剩下的一个荷包蛋,丢下筷子就往外跑。

草把子烧的炊烟渐渐散去,女孩们的歌谣由远及近。“天上雾沉沉啰,地上闯麻城,麻城闯不开,把那个小子带过来。”吼啊,吼啊,二十多小伙伴们前后牵着衣襟像摆龙灯一样荡漾着,追逐着,唱着歌谣玩捉迷藏。感觉这是小女孩们的游戏,我们男孩要玩打仗。悄悄拿出父亲单位的几本材料纸,我跟母亲的学生们换来了梦想的一切:有弹弓、黄泥巴枪、炮炮枪、打火柴棍的链子枪。扎上父亲的皮带和枪套,戴着盖过耳朵的军帽,我俨然成了伙伴们的司令,一大群孩子们屁颠屁颠簇拥我,看哪个不服,我们就把他五花大绑,平定了几个小刺头,我们分两队打仗。队里稻场就是我们的战场,几天激战中,大队诊所的很多针头(用作炮炮枪枪头)不明丢失,几个草垛被攻垮,茅厕的矮墙不幸倒塌,几堆柴火散落一地,稻场到处是石子、沙土、火柴棍,水狗队长拿着扫帚追着我绕塘跑了一圈,我立即躲回家,几个有一点点破皮流血的小家伙却不依不饶,哭着找上门扯皮,母亲拿出云南白药与酒调好,一一敷上,还进屋抱出一陶罐,一人喂一勺红糖,小家伙抹去泪涕,笑嘻嘻回家。夜幕降临,隔壁的小安、冰冰家里传来了杀猪般的号叫声,父亲没收回他的军用品,阴沉着脸,来回踱了几圈,让我在地上跪了整整半个钟头。

五月的麦田莺歌燕舞,碧绿无垠。村北边的麦田紧挨着小安家的后门,这是我们的乐园。放学回来,我们四五人在小安家做完半小时作业,马上溜进麦田。浅绿色的野莫芄缠绕在碧绿的麦秆上,紫白相间的小花开在上面,在泛青摇曳的麦穗中若隐若现,我们争先恐后将野莫芄的花藤抽出,缠成圈,戴在头上,感觉成了《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匍匐在麦田里狂喜,然后一口气猛吃青嫩爽甜的小豌豆,打着饱嗝,吹着用麦秆芯做的哨子,满载而归。突遇回家的父亲大发雷霆,揪着我的耳朵,大吼一声跪下,隔壁三家都听见他的训斥:“麦秆一抽就没有小麦,谁叫你吃队里的豌豆?吃了还敢往回偷?”双腿有些酸麻的时候,母亲叫我写了检讨书。即便在瓜果飘香的夏季,我也能抵挡住诱惑。北村的粮,南村的瓜,那时绝对是纯有机农产品,靠近河的南边几十亩瓜田,苍翠欲滴,香甜诱人。尽管有人照看,但每天都有小孩被捉,大人也牵扯进来打架,后来队里终于发生争执,因照管不力、分发不均,大家一哄而上,居然把成堆的瓜果踩得一塌糊涂。沮丧的水狗队长第一次摸着我的头,对我说:“你没偷过,好样的!”

“嘶呀,嘶呀……”蝉鸣越来越令人烦躁的时候,人们离不开水塘。酷暑时节,大人们只穿一大裤头,我们男孩干脆赤条条一丝不挂。河里又宽又深,每年都有人溺水而亡,大家都怕;大塘里长满了红色菱角和绿色的猪草,不知深浅,我们不敢去。连通大塘的村外有个小塘,较浅,是村里吃水塘,清澈见底,不见一条鱼,没有人在里面游泳。我和文生、小安互相怂恿,摸着塘坡入水,玩得兴起,胆子越发大起来,文生要往塘中间游,突然滑入淤泥中,我俩赶紧去拉,三人立即同时陷入泥中,呛得水泡翻腾,只剩下几只手在水面上乱抓,辛亏村里傻子光法看见,救了我们。闻讯回的父亲依然罚我跪下,平静地拍着我的肩膀告诫我:“养大你不容易,以后游泳必须跟大人。”母亲不放心,用毛笔在我的肚挤眼画圈,每天回家洗澡前不见墨圈,则要挨揍。其他父母纷纷仿效,自此村里很少有小孩溺水。后来,长辈们带着我们,很快学会了游泳,我一样可以一手举着衣服,横渡两百米宽的河面,帮忙大人们来回运花生。

十二岁那年,我们全家随母亲住校搬出了老家。放暑假时,父亲坚决带我回老家帮伯父干农活。分田到户后,家家都有吃不完的瓜果,他们把我当客人样款待,但再也感觉不到原来的味道。伯父一再嘱咐我割麦腿要张开,不到十分钟,我还是把自己左腿割得血流,伯父干脆叫我捆麦穗,半天下来,忽然感到双臂火辣辣地痒痛,全部长满红疙瘩,虽然强忍着泪水,慑于父亲的威严,仍不敢回家。坚持到插秧的时候,我也成为分秧甩投的好手,伯父为了秧苗成活,还是没有教我插秧。傍晚,劳累一天的人们停歇下来,长辈们用艾草在稻场边生着几堆烟,各家搬出条凳,搭上圆簸箕,里面铺好棉絮凉席,我安然躺进里面,伯父大妈打着蒲扇,静静地听着村里老会计讲三国赵子龙的故事,四面八方的蛙叫声此起彼伏,在稻田旁萤火虫忽闪忽闪的朦胧中,我一次次沉沉睡入梦乡。
责任编辑: 刘君